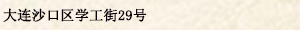朱小蔓教授纪念专刊朱小蔓我的初中生活
我的初中生活
文
朱小蔓
我的初中阶段正遭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城市家庭也几乎无一幸免地粮油肉蛋配给得更少,难得吃到肉不说,蔬菜也基本上天天吃“飞机包菜”(即长得极为粗糙、叶子大,颜色青紫色、其实包不起来的所谓包菜)。听同学说他家附近有几棵槐树,母亲让他兄妹几个去摘槐树花,回来和面粉擀面皮儿吃,算是孩子们心目中的美食了。那段日子每天上午 一节课,同学们常常饥肠咕噜,盼望下课心切。有几个男生竟发现太阳光照到教室窗子的哪一块玻璃就是下课铃快响了,于是提前收拾好书包,铃声一响,随着一阵哄叫、一溜烟地冲出了教室。因为缺乏营养,我们全家人的脸、双脚,甚至小腿都浮肿起来。我个子长得早,初一时就已经1米60,由于营养供给跟不上身体的成长速度,患上了心肌炎,体育课的不少项目不能参加,比如游泳课不能去,一辈子都是“旱鸭子”。当时为了支援近郊农民养猪,要求学生每天打猪草,捞水浮莲,早上上学时提着网线兜,在校门口过秤、记录后上交。那时我们还去郊区人民公社帮助秋收。初中生虽有班主任老师带着,但许多事儿都由班委会领导同学们做的。比如来去都用板车,拖着大家的行李,步行过去;在乡下住进老乡让出来或公社空着的简陋房子里,有的甚至住在老乡腾出来、打扫干净的猪圈里;晚上睡在垫着一层稻草的地铺上,夜里用粪桶当尿盆;干的是些除草、收庄稼、积肥等活。当时的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初中生,可以像大人一样独立做许多事儿了。
……
初中生还是有点调皮,爱给同学起绰号,拿同学开玩笑,甚至对老师也是如此。初一时的班主任兼教地理课的刘默然老师说起话来有个下意识地时不时揪揪领子的小动作,课后同学就模仿他,常常引起一阵哄笑。那个年龄的我们分男女界线,课桌多有所谓“ ”,井水不犯河水。最记得的是我后排课桌的男孩有一次用两根绳子把我的辫子拴在他的课桌腿上,害我站起来一个大趔趄。还是这个淘气的男同学有一回竟从我背后把爸妈给我买的白底红点新衬衣背部的红点全用墨汁涂成了黑点。我没向老师告状,但又气又心疼,自己哭了一场。好在回家后爸妈倒没说什么,事情就那么过去了。那时男女生间会拿小说和电影中的角色来开玩笑。当时正流行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于是有同学叫某个男生“少健波”、某个女生“小白鸽”,给配上对儿,本来完全没影儿的事儿,弄得被玩笑者双方倒不自在起来。
……
那时的课堂学习并不紧张,从没觉得有什么负担。教师的教学似乎也没有今天那么多教学法。每个教师上课各有特点和所长,有的几乎是满堂灌,但因为讲得精彩,也能攫住我们的心。有的老师提问多,有的老师课堂训练多些。记得历史课陈丛天老师知识渊博、教课特棒,同学们很佩服他。我不喜欢记忆,而且记忆力不强,历史课学的并不好,但这位老教师头上那几根稀疏的白发在摇头晃脑时飘动起来的样子倒是记得蛮清楚。化学课盛翠英老师正中年,常穿一件青黄色英国格子呢西服,后来同时又做我们的班主任。还是因为不喜欢记背,我对学化学不大感兴趣,学得也不怎么样。但盛老师常常让我们用画图来表达化学知识,我倒是很喜欢,不仅画表格,连烧瓶、 、漏斗什么的都画得十分用心,工工整整地画了两本练习簿,赢得老师数次表扬,后来也就不太厌烦化学了。对语文课印象深的有学习高尔基的《海燕》一文,那不仅是文章本身优美而有气势,也是因为老师让我站起来朗读,还让我去参加什么比赛,为此,我还主动去找当时学校里新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在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共青团员大学生之一——陈平老师做过辅导。对古文教学印象最深的是学《曹刿论战》,记住了文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指挥谋略。还有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老师让我们反复吟诵,其中“布衾多年冷似铁”“两脚如麻未断绝”,在我们日后只要陷入困难生活时就很容易被联想起来;我们还分组轮流大声朗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那忧远的平民情怀、深刻的思想性比在小学时学的哪一首杜诗都要更吸引我。俄语课印象最深的是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还有一些俄罗斯寓言故事。遗憾的是当年基本学的是哑巴俄语,教材政治内容偏多,反映建国前后英雄人物的故事多,而日常交流用语少;无论是课本本身还是课堂口语练习都远远不够,如此,生活中也就很难用得上。对于数学中的平面几何,由于老师教的好,思维清晰、推理严密,而且特别有本事引发我们对于添加辅助线来解题的兴趣和好奇心,于是特别喜欢这门课,不仅能很好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主动、积极地去做大量习题。那时用的都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由国外翻译过来的习题集,几乎没见过什么国内名校、甚至教师自编的、用于提升考试成绩的教辅材料。习题集上的题目与平时考试及升学考试没什么关系,习题也完全不是学校和老师要求我们做的,但许多同学都发自内心地情愿做。我也做得特有兴趣,兴致盎然,好像并不为什么,就为每解出一道题时那种快乐无比的自豪感。前年,我从中华读书报上读到福克纳年获诺贝尔奖的演讲,他说自己“也不仅是为了荣誉,为了利润,而是想从人类精神的材料中创造出某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东西”。我们虽不是伟大科学家的材料,也没想到能创造什么。多年后同学聚会谈起当年这个课外嗜好,大家不约而同地说,那纯粹是因为做那些难题挑战自己的毅力和能力,很好玩儿,精神上有极大的满足。那年头的家庭作业一般不会做到晚上,下午很快就完成了。更没有家长过问我们的学习,尤其是检查作业什么的。课余时间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从没有被逼着做作业,或为了排名对付考试的经历。父母亲忙于他们的工作,从来不管我们的学习,也从不问考试分数、排名第几什么的。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感受到的只是父母对我的慈爱与信任。
当时的初中生是有时间课外阅读的。我自己和周围同学们大多读过长篇小说《红岩》《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三家巷》《青春之歌》《家》《春》《秋》等,中篇小说有《夜半鸡叫》等,短篇小说多为苏俄小说,如:契科夫的,长篇的有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是文学作品刻在我们身上的主要印记。同时也有些写上海民族资本家、写国民党人物故事,增加了我们思想的复杂性,也留下一些疑或不解。年建国十周年时全国上映过多部国产新故事片,如:《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林则徐》《五朵金花》《回民支队》《早春二月》等,都是可以载入新中国电影史册的。我和同学们都是既看了电影,又回来找小说读。那个阶段我正处于青春时期,对理想、对英雄,对友谊、爱情,对善恶是非、对美都抱有纯真而朦胧的憧憬,这些书籍、影片以及父母给我订阅的《少年文艺》杂志、《中国少年报》等都是陪伴我成长、影响我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来源。
年初中毕业,我接着报考本校高中。我们班上部分同学主动去考中等师范和中技校。那时的南京有一批中技校办得很好,在全国都有名气。这类学校的考分与南京市几所最强的高中录取分数线基本持平,有的还稍高一些,比如: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蜚声中外,常有外国元首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亲自陪同参观该校;一般是学习成绩好,但家境较为贫寒的同学最理想的求学之地。我所记得的班里的女同学杨辉银、陶宗玲考取了当时 的中技校,很让同学们羡慕。
现在都说初中生难教、初中校难办,一是因为学习成绩在那个阶段特别容易出现分化,二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容易造成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的紧张。但我的初中生活,我所在的九中初中当年并没有给我留下这种负面的明显记忆,这究竟是囿于个人生活圈及其交往的限制,没有在这方面有更多发现呢?还是当年的时代文化、社会风尚,九中端正的校风使得它们并不那么彰显呢?现在我们动辄青春期逆反心理问题究竟是完全真实的现象,还是接受心理学某些理论的影响和暗示或者是时风舆论、同辈影响而将其过分夸大呢?所谓初中生难教是不是还存在着初中课程,尤其是数理课程在难度设置上有所偏差呢?是否还存在着初中学校资源配置上相对较为薄弱,部分初中校长在办学思想、校园文化建设上有工作欠缺以及教师在师生互动、应答学生情感需求方面有能力上的不足呢?我没有做过深究,所以想不清楚。
本文节选自《中小学班主任》朱小蔓教授纪念专刊《我的初中生活》。
朱小蔓教授纪念专刊谨以此刊向朱小蔓先生致敬
9月13日限量发行点击购买目录学养深厚,道德纯粹
卷首论语
1/ 的传承崇高的敬意深切的缅怀/陈萍
朱小蔓生平简介
小蔓追怀
6/怀念父亲——我的遗憾与告慰/朱小蔓
10/我的初中生活/朱小蔓
13/直把万安作故乡/朱小蔓
家人缅怀
16/无尽的思念/吴姗
18/生命中懂我的那个人,走了/朱小棣
青蓝情愫
21/海燕依旧在翱翔/陈平
22/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