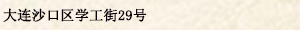大麥陪读
白日耕田夜读书点击上方“耕读吧”
陪读
文/大麥
壹
狗剩圪蹴在上房地上,把头戳进两膝盖间,任由泪水哗啦啦流,他没脸放声哭,也没脸面对头跟面碗一样的父亲,更没脸瞅一眼可怜的儿和女。他的眼前,是一滩挏浑的水,看不清成色,看不见天日,看不到希望。“狗剩,狗剩,日头都照到当院了,咋还不做饭呀!”蜷缩在炕上的二拐老汉嘟囔一句,抖动身子咳出一团浆糊一样的浓痰,嗬哕一声,哕到地上。狗剩起身,跷过父亲刚哕到地上,还冒着热气的浓痰,出了上房门。盘腿坐在炕上看书的念娣,拍拍爷爷的后背,说:“爷,你好好缓着,我爸做饭去了。”“娣娃,帮你爸烧火去,叫堂娃来给我捶捶背,心上跟压了块石头一样,难捱的很。”二拐老汉用肘子搡了搡孙女。念娣偎了偎,腿搭到炕边,地上除了爷爷刚哕的一坨痰,还有爷爷破船一样的两只布鞋,不见了她白皮皮的鞋子。那白皮皮的鞋还是妈妈去年给她买的,穿着可舒服了。除了上学,她平常绝对舍不得穿。“爸,爸爸,我白皮皮的鞋子咋不见了?”“刷了,晒晒,娃陪爷爷,到炕上看书,一会会就干了。”念娣又偎到爷爷身边,说:“爷,我给你捶背!”二拐老汉嗓子眼里像扯大锯,呼噜噜直响,他左肘支炕席,右手摸索着抓住炕沿,晃荡了两三次,才将躬成?的身子翻转成后倒的D。念娣熟练地把枕头塞到爷爷的肚子下,背却像老牛脊背一般曲折地隆起来,像张弦贴炕面立着的弓。二拐老汉刚过七十,不算老。他的背早早驼了,出门进门一百来斤的担子在肩上压着,能不驼?庄农人,只要家里安生,娃娃们的日子好过,背驼也就驼了。人活一辈子,像春种秋收,如果年景不好,赶上夏旱或涝了,秋收无望,那下一年就不种庄稼了?不能,还得撅起尻子了干,这就是庄农人对土地的坚守,也是对生活的坚守。说来,二拐老汉也是个命苦人。他三十二岁那年,老婆子撇下他和狗剩,到天上享福去了,那会儿刚包产到户不久,大家伙儿疯子一样,起早贪黑在黄土地里挖壮辣辣。土地是庄农人的命根子,人哄地一时,地哄人可是一年,没谁敢大意。狗剩那会儿才八岁,他是既当爹又当妈,还要伺候十多亩地,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狗剩,他可真是犯了难心。饥一顿饱一顿,生一顿熟一顿,二拐一手拖着狗剩,一手牵着驴,坡坡屲屲,沟沟壑壑,父子俩相互陪伴着,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走出了苦难的日子。“哎——哟,哎——哟哟,娣娃,就这,拳头子摁!”二拐老汉眉头拧成了疙瘩。“爷,你脊背的骨头硌得很。”念娣跪在炕上,两只手捏成拳头,在爷爷背上来回摁、反复搓。贰
年,眼看着到了跟前,家里烂包得没眼儿看,狗剩心乏得像破棉絮,没地方拾掇。娃他妈叫顺瑛,前三年一直在县城陪两个娃娃念书,儿子王念堂刚上初二,女儿王念娣才上小学五年级,这歹毒的女人咋就能忍心撇下俩娃娃跟人跑了呢?二拐老汉想不明白,成夜成夜睡不着,长叹短叹。狗剩更想不明白,家里日子虽然烂包,但他没亏着她顺瑛呀!他拼了命营务苹果树和麻椒树,也种了些口粮和蔬菜,一年现钱也能收入成十万元,供娃娃上学,家里开销虽不宽裕,紧巴紧也能过。前几日,狗剩恓惶得受不住,提溜了瓶三星金徽酒寻摸到罗存有家,这人虽说也务农,但活泛,有想法。他想灌两盅盅酒了,倒倒苦水,好让存有帮他拆解拆解。存有把狗剩让在沙发上坐,他拿个碎板凳坐对面,酒过三巡,狗剩脑袋胀乎乎的,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断断续续讲述着他的过往。“三哥呀,你是知道的,我爸这辈子苦,可我也不易呀,你说是不?唉,到我手上,是把人活倒糟了,家家没经营好,女人女人跟着人跑了,我还算是个男人吗,三哥?“三哥,你在咱一伙伙庄农人里,是人尖子,你给我说说,我到底是哪儿做错了,还是做过啥亏心的事了,啊三哥?“不瞒你说,三哥,我心上跟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没处说,难捱的很呀呀,我听着我爸长叹短叹的叫唤,死的心都有,可我死不起呀三哥,我没孝顺我爸不说,俩娃娃还碎碎的,没成人,要是娃娃成人了,我死也就死了,唉,三哥,我过得难场不?“三哥,你说说嘛,顺瑛我没亏着她吧,好吃好喝好穿着,我都是尽着她和俩娃娃,我和我爸天天凑合着对付三顿饭,身上没沾过一件新展展的衣裳,我爸一年四季两只光脚片子,这阵儿脚后跟裂开的口子连碎娃娃的嘴一样,我看着心拧着疼呀,三哥!”煤炉里的火呼啦啦地叫唤,他俩像是关进了炉子中间的烤箱里,温水煮青蛙一样,把身体里的水份一点一点烤走。存有时不时劝句“喝口茶!”再没接话,他抿口茶,深深地吸口旱烟卷。存有手头宽裕着,他能抽得起纸烟,但他嫌纸烟没劲,一直用报纸卷指头粗的旱烟抽狗剩用袖子擦擦鼻涕,接着诉说。“三哥,我寻你来,是想请你给我拿个主见,我这日子到底该咋的往前推嘛,三哥?人活到我这份上,也不怕三哥你笑话了,没一点点意思,真格没意思……”存有没说什么。他经得多,看得也多,但他不敢这会儿给狗剩瞎指点,弄不好一家子人就没搭救了。一瓶瓶酒,俩人晃荡来晃荡云,碰完了,狗剩哭诉得也没言语了,存有喊老婆子:“掌柜的,他王家爸要走。”存有家的硬把个篮子挎到狗剩胳膊弯弯上,拍拍打打送出了家门。叁
狗剩思前想后,年货还是要置办的,天没塌下来,就是真的塌下来,他也得挺直了腰杆顶着,一家之主,就得有一家之主的样子和担当,哪有见事就躲避的道理。腊月二十八,他带着儿子和女儿进趟县城,给俩娃娃每人买套新衣裳,新鞋子,给老爸称二斤上好的茶叶、白沙糖。完了要再割几斤羊肉。前些日,存有家嫂子给了一吊猪肉,有四五斤,还有一大块豆腐和一碗荞粉,这人情是欠大发了,他狗剩得记着。老爸一辈子念叨着个羊肉汤,他得割几斤,过年了熬成羊肉汤汤,再撒一把芫荽,让老爸解解馋。日子再恓惶,不能苦了娃娃。到了县城,他给念堂五百块钱,叮嘱道:“狗狗,你俩看着把结实耐穿的买上,一人一身衣裳一双鞋。买上了,到三小念娣学校门口来!”狗剩打发走儿女,弓腰塌背,两条腿像猪大肠,软塌塌的,脚跛踏跛踏搓着马路往菜市场走。他边走,边思量,得把羊肉先割上,顺手买些菜,再拐到牟家巷称茶叶和白沙糖,茶叶得称两份,老爸一份,娃外爷爷一份,还得买瓶好酒,给存有哥拜个年,这情分得续着。腊月的菜市场像口大炒锅,吆喝声、问价声、讨价还价声、熟人打招呼声一股脑儿倒进大锅,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炒,越炒越有年味,越炒狗剩的心越焦。他在心里嘀咕,光阴好的人过年图个热闹,我狗剩过年就过个难场和挖苦呀,唉……狗剩双手筒袖筒里,被人流裹挟着,踅摸他心目中的猎物。“蒜苔几毛?”他指了指菜摊上一捆一捆码得整整齐齐嫩汪汪的蒜苔,头勾着,几个字像是从裤裆里挤出的。“几毛?哪还有几毛的菜?六块,要不,刚开箱的,嫩的很!”摊主硬硬地撂下一串话,忙他的事了。狗剩被人群挤着往前挪。“他娅娅,菜花多少?”“便宜,便宜,这一疙瘩有个三斤,我给你称,看看,三斤一两多,给十二块,零头抛了,给给,塑料袋袋装上!”“再给一撮芫荽。“能行,给,就不称了,这么大一撮,给一块钱算了,都不容易,过年哩,图个吉利嘛。”狗剩刚挤到马家羊肉铺前,有人迎面嚷:“王家爸,嘎,有两三年没见了,屋里都好吧,我爸一直念叨着要看王家爷来,看过年天爷好不,好了我开车送我爸来看看王家爷。”是南川来亲戚,狗剩点头哈腰地应承着,人浪把亲戚卷走了。“师傅,割上三四斤,肥瘦匀称的,熬羊汤汤喝。”“这块,后腿肉,煮来炒来熬汤来,都美的很。”一刀下去,五斤二两。“就这,过年了,算便宜点,共二百四十三块三,零头算了,给个整数二百四,能成不?”狗剩咬咬牙,“能成,能成,剁剁,碎疙瘩,我好拾掇,麻烦了!”狗剩把计划好的东西都买齐后,拐七拐八到女子上学的三小门前,路边吆喝着“麻子,麻子,特大麻子。”他把手伸进棉袄,捏捏兜兜,硬硬的,东西安全。他磨蹭半天,抽出手,手里捏着一张拾元的票子。“给我称上拾块钱的。”他圪蹴在马路牙子上,吧唧吧唧嗑麻子,麻子皮皮,一撂一溜黏下巴额上,像一坨蠕动的细腰蚂蚁。嗑着嗑着,嘴里就寡寡的了。他卷了指头粗的一棒旱烟嘬到嘴上,打火机呲咣呲咣打了三四五下,风大,打不着。狗剩解开棉袄扣子,左手扽着衣襟,右手戳进怀里,呲咣,着了,憋口气点上烟。鼻涕像两根手擀粉,刺溜滑了下来,他左手拇指和食指一捏鼻子,擤了,手在脚帮上蹭蹭。“爸,你都买上了没?”念堂拖着念娣的手,气喘徐徐的。“好了,好了,你俩买上了没?”“买上了。爸,那儿有卖烤红薯的,给我爷买两个吧?”“能行,买上,等着,钱。”狗剩说着,手戳进棉衣里摸索。“有咧,有咧。”念堂拖着念娣的手走了。肆
看着念娣摊开的衣服,狗剩鼻子一酸。他咬咬牙,没让酸楚的泪水当着儿女的面流下。他拾掇了三支香和一撂票票,给斜坐在炕上的老爸说:“爸,我去看看我妈去!”没等二拐老汉反应过来,他已经飚出了房门。“你爸咋了,怪怪的。”二拐老汉嘟哝道,“狗狗娃,给我背上挠挠,骨头缝里痒得难受。”念娣爬上炕,手从爷爷的后腰伸进衣裳,“爷,忍着些,我的手冻的很。”狗剩勾着头,出得门径直往坟地里奔。他的步子有点零乱、有点急促、有点伤感,憋了一肚子的苦水,没地方倒,年头节下的,他突然想妈妈了,他来给妈妈烧点盘缠,也想给妈妈诉诉心里的苦。妈妈的坟头被蒿草覆盖得严严实实,他后悔来得匆忙,没带把镰,好给妈妈修整修整院落。撂荒的阴宅和倒塌的庄院,是这些年农村最直白的画面。在脱贫致富目标的引领和城镇化浪潮下,富裕的梦想裹挟着千千万万的农民涌进城市,抽空了广大农村的新鲜血液,农耕文明的精神家园,如敝屣一般被丢掉了,原本的稳定被颠覆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撂荒土地”成了广大农村地区普遍的底色,也是时代的记忆。狗剩拔掉妈妈坟头前的荒草,用脚踩踩,扑通双膝跪下,颤巍巍点着香,插到松软的土上,又呲咣呲咣打着火,点燃冥币,跳跃的火苗印出一张棱角分明、线条硬朗的脸,他曾也是妈妈怀里的宝呀,可妈妈躺在地下几十年了,他却被生活盘得支离破碎,想着想着,狗剩哇地一声哭了。四十来岁的男人,干瘦的身子抽动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对着自己至亲的妈妈,像小时候那样,一股恼儿把所有的委屈化成泪水和哭声,排山倒海般倾倒给妈妈。“妈妈呀,叫我咋的个活呀妈妈,不是我不下苦,懒散,也不是我不尽心操持,可这个家咋就让我操持成这个样子了呀,妈妈……“妈,我媳妇顺瑛,撇下家,撇下娃娃,跟人跑了,人家要过城里人的日子,嫌咱这穷土窝窝,没办法,拴住人留不住心,枉然。我不怪她,是我没本事,连个媳妇都拢不住,就是可怜俩娃娃了,一口热饭吃不上,唉,妈妈呀……“妈妈,我心上结得实实的,没处说个话,眼瞅着过年了,我来看看您。妈妈,您一个人在那边,照顾好自己个儿,别惦家里头,给您说说,我心里就敞亮了。放心吧妈妈,我能挺过去,我爸身子明显不如去年,也是操我操的,年后了我领着看看去。妈,您好好的,想您呀妈妈!”狗剩把一肚子的苦水倒给了妈妈,心里一下子畅快了,像是把千斤重担卸给了黄土下的妈妈,妈妈还像他小时候那样,把他护在身后,自己迎接所有的苦和难。这念堂和念娣俩娃娃倒是有主意,他安顿得好好的,让给他俩各买套新衣裳、新鞋,这俩狗倯偏拧着来,他们给自己各买了一双鞋、一双袜子,剩下的钱,给他爷买了件上衣、一双软底布鞋、两双袜子,给他这个当爸的也是买了件上衣、一双运动鞋、两双袜子,还给他爷买了个竹子做的痒痒挠。唉,这俩娃,懂事得让他这个当爸的心跟千万只小虫子咬一样难受。别人家这么大的娃,父母当宝一样娇惯着,他的娃却要早早分担家里的责任。念堂放寒假以来,领着妹妹做饭,还说下学期,他就能照顾妹妹了。他娃不照顾妹妹还能咋,在县城念书,一日三餐得吃呀,自己做能省点,如果顿顿买现成的,他供不起。之前他妈妈说是纹丝不动伺候俩娃念书,结果一捋风就把她的心吹化了、吹散了、吹乱了,十多年的夫妻情分不要了,家家不要了,俩娃也不要了,说是跟着个南方来摆摊摊卖狗皮膏药的男人,头也不回走了,这女人的心,咋的就这么硬嘛!狗剩想不明白的事还很多,他就念了个初中,认识的字也能装一背篓,但很多道理他还是拧不过弯,很多问题犹如肠梗阻,梗在那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越结越大。他在日日夜夜开导老爸的过程中,自己慢慢开解了不少结。人家顺瑛长得心疼,比他还小九岁,今年实岁才三十二,可长得像是二十二三的样子。一米六二的个头,脸上光光滑滑的,眉脸儿俏得很,瓜子儿脸蛋,大眼睛,双眼皮,鹰勾鼻,碎嘴巴,鹿一样的脖子,身材也展脱得很。刚结婚时,他粗糙的手,滑过人家的身体时,有种惶恐感,他觉得她是绸缎,他粗糙的手挼揣这么高级的绸缎是暴殄天物。他甚至想,她嫁给他就是个错误,明媒正娶时,她是乐意的,她还换着花样伺候他。白天,想着黑了能搂着天仙一样的女人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一身的牛力气,一夜一夜在她身上耕耘,她咬着他的耳朵说美的很,一辈子这样伺候他,让他美美的快活着,过好日子。说过的话,咋就像放了的屁,说变就变了呢?狗剩想明白了,变就变吧,自己的日子还得自己过,变了的心就是拢回来,也马蜂窝一样,没眼儿看了,随她去吧。他不信凭自己的一把子力气,抓养不大两个娃娃。伍
没女人的年,过得凄凉。俩娃娃帮着狗剩,对付着一日三餐。他爸爸有两个娃娃天天陪伴着伺候着,精神头明显好转了些。狗剩一个劲儿说,爸呀,你就想开些,咱的光阴还得咱自己刨,你攒攒劲劲的看着家门,我给咱苦庄农,两个娃娃到县上好好念书,咱四个人拧成一股子绳,就是绑也要绑上狗日的穷日子往前推,等娃娃都上了大学,咱就出头了。春暖花开,各种蛰伏的虫虫从土里钻出来,探头探脑,伸腰撂胯,四处寻觅着、试探着、占领着。狗剩年前把苹果树都修剪了,春风一吹,枝条开始泛绿,嫩芽芽像小媳妇受孕后的肚子,见天凸起。他趁着农闲,先人一步修整果树地,把就要吐芽的野草连根拔起。地就是他狗剩的命根子、钱匣子,他指望着地里长出供娃娃上学和维持家用的费用。等,没用;抱怨,也没用。唯有干,才是解脱困境的办法。这道理,他狗剩明白。二拐老汉也能拄个棍到院里院外遛弯,狗剩的心算是捏到一块儿了。念堂领着妹妹念娣在县城念书。他除了管俩人的一日三餐,还要辅导妹妹的作业。两所学校相距不远,他上学要路过妹妹的三小,这样上下学,他都拖着妹妹,风雨无阻。每两个礼拜,狗剩都要带着面、洋芋、包包菜、粉条等来看他们一趟,把他俩的小屋拾掇拾掇,拆洗一下被褥,再留下足够的生活费后,把一筐筐的叮嘱打包留给俩娃,拍拍念堂的肩膀,摸摸念娣的头,恋恋不舍地走了。每次来时,狗剩心里焦了一样,他想快快看到自己的娃儿,看他们好着没,有没有感冒,而返回时,心头总是酸酸的,他亏欠娃儿们,让丁点儿大的娃娃自食其力,这父亲当的呀太不够格,太不够格!有时他也想,这可能就是他们老王家的命。自己个儿早早丧母,小小年纪就跟着父亲饥一顿饱一顿过日子,哎,不敢回头看,那不能叫日子,只能说拉条人命,活着。这俩娃虽然比自己幸运,光阴稍好些,饿不着也冻不着,但没妈的娃娃究竟少了半拉天。他没办法给娃娃母爱,就尽力照看好一亩三分地,把苹果树和麻椒树营务好,让娃娃们别少吃缺衣。穷光阴有穷光阴的推法。一来二去,日子驴推磨一样一圈儿一圈儿推着转。念堂娃争气,考到县一中的重点班,成绩还一直拔尖。念娣上了初中,反过来照顾上哥哥的一日三餐,她一直说,哥哥你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我来照顾咱爷和爸。念堂嘴上不说啥,抓妹妹的学习不松劲,妹妹的语文稍微差点,他分析后认为,主要是阅读量不够,作文是最大的欠账。假期里,他把妹妹圈在爷爷的炕上,炕头撂了一大撂书让她读,家里家外他帮着爸爸,不让妹妹插手。有天晚饭后,爷爷佝偻着蜷缩在炕上叭叭抽旱烟,念堂突然问妹妹:“假如作文题目是《我的爷爷》,你想咋写?”念娣偎到爷爷旁边,“爷,您爬下,我给你挠挠痒痒了编作文。”二拐老汉乖乖爬展脱,孙女挠痒痒可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享受!念娣边挠边说,哥,我这么想的,说个大概。开头先交待爷爷的身份,打个比方,嘻嘻,比方是个完倯,我老爱打它。“我的爷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在我心里,爷爷是天底下最好的,因为他爱爸爸,爱哥哥和我。就这么开头,行不,哥?”“连住,说思路。”然后,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写爷爷的勤劳,我想主要以听爸爸说的方式来叙述,增加真实感。第二个层次,写爷爷的坚韧,主要写爷爷操持家的不易与艰辛。第三个层次,写爷爷对我的爱。哥,你别吃醋,爷爷更爱我,对不爷爷?二拐老汉舒坦得不要不要的,他含糊地说:“我的娣娣娃最心疼。念堂默许地点点头,“没大问题,但要记住,我们是写命题作文,重点的重点是抓住主题,开宗明义,结构合理,逻辑严密,首尾呼应。虽然文无定法,但我们是中学生,更多的是打基础,在把握好各类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再图新义,千万莫本末倒置,等以后有能力搞创作了,再深挖题材、立意、章法等等。写人物,一定要有细节描写。就像《背影》里,写父亲爬月台时吃力的样子,几句话就把父亲笨拙、年老体弱、身体微胖等特征简笔画一样勾勒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细节,把父亲对作者的爱表达的淋漓尽致。”“堂堂,你爸在哪儿爬着呢?”二拐老汉突然插话,惹得俩娃娃和圪蹴在地上嘬巴旱烟卷的狗剩哈哈大笑。久违了的笑声,穿透窗户,穿透院墙,穿透夜空,在半空中盘旋回荡。陆
“爸,爸,你跟我爷说,我哥的分数出来了,,能走很好的大学。”接到念娣的电话,狗剩扔下手里的活,一奔子蹿回家,气喘徐徐地对坐在房檐下炖茶喝的老爸说:“爸,爸,娃刚来电话,出来了,。”“慢些说,啥出来了?”“堂堂的分数,高得很,能走个好大学!”“我的堂堂攒劲的,咱祖坟上冒青烟了。”二拐老汉伸出枯树杈一样的手,奓着大拇指。黑洞洞的嘴咧得像小孩。“娃打工挣学费着,我打电话叫回来算了。”狗剩征求老爸的意见。“电话打个,来不来,听娃的。”二拐老汉似乎比狗剩更懂孙子的心思,把话说活,甭难为娃娃。接到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念堂才回到家。高考一结束,他就跑到省城,在快递公司分拣货品,大概干了一周,有位送快递的大哥家里有事,他临时接替送起了快递。更重要的是送快递挣的钱更多。他骑着电动三轮车,开启导航,在这个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他不觉得累,他更多的是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妹妹的未来、爷爷和爸爸的未来、家的未来。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在街上溜达,街旁商户五光十色的灯光,把街面照得像玻璃镜,幻化出各种奇异的图案,他置身其中,仿佛世界换了个模样。念堂惊奇地发现,在广告牌和一坨坨树阴里,散落着一位又一位衣着暴露的女子,她们明目张胆向过往的男人抛着各种媚眼,有的还无耻地伸出手来,用食指勾来勾去。念堂知道她们是干么的,他加快步子,想尽快逃出这迷幻之地。突然有只手揪住他的肩袖,扽了扽,他扭头睃了一眼。“帅哥,玩玩呗!”像呕吐物喷了他一脸。他睃过去的眼睛钉在那张脸上,这张脸是多么熟悉啊,她在梦里一次又一次出现,他哭着喊着想抓住她的衣襟,都被她残忍地拒绝了。他的呼吸急促得快要窒息。“走嘛帅哥,可好玩了!”她还在卖弄,她还在勾引,她还在拉生意。“刘顺瑛!”他突然脱口而出,叫出了这个名字。他多么希望,多么希望这张脸是个赝品,与那个深藏在他心底的名字,根本不匹配。可那张糊了厚厚粉黛也遮不住岁月流失的脸,唰地青了,又瞬间红了、黑了,涂得像吃了死娃娃的猩红嘴巴张着,眼睛瞪得铜铃一样。“刘顺瑛,妈——”当念堂再次从丹田处生硬地叫出这个美丽的名字和伟大的称谓后,她像支离弦的箭,嗖地,穿马路,射向人群,射向看不到边的黑夜,不见了……念堂定定地站在那儿,傻子一样,他脑袋空空的,什么也没想,什么也不去想。闪烁的灯,没命地变幻着色彩,似乎要穷尽人间所有的冷嘲与热讽。“你妈是婊子”像乱箭,从四面八方袭来,他疯了一样跑呀跑,跑呀跑。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个梦。可那张脸像魔鬼一样,只要他闭上眼睛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假惺惺地说:宝贝,妈妈爱你!这一天是8月7日。念堂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