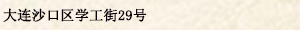家渑池文苑沈文兰
昨夜早睡入梦,梦见自己超人般飞越时空,鸟瞰连绵起伏的群山,竟然是个阔大的“家”字,偃卧着在喘息,它需要我来拯救。用双臂托起宝盖头,咬紧牙关,倾尽全力……
1一直认为,我的家与这个小城的建设和发展一样,是凝重而又质朴的。
25岁的父亲抱着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姐姐,母亲牵着3岁哥哥的手,后面跟着奶奶,一起走进这个面积大约7分地的小院。坐北向南的4间小瓦房,没有围墙。在没有爷爷的帮助下,父亲靠自己不很成熟的泥瓦和木工技术,用不多的钱建成了这座小房。爷爷出差回家,看到赫然矗立着的4间小瓦房,激动地说:我儿子真的撑起了这个家,造起了房,比我有本事,我可放心了。如果它现在依然存在的话,应该是知天命的年龄了。我7岁时,父亲早已不再从事泥瓦和木匠工作,他在煤矿上班,而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他们除了养活我们姊妹4个,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家的改建工程中。
每日下班,父亲会带着哥哥、姐姐,甚至母亲,到已经荒废的沟沟沿沿拾石头捡砖。院子的下半截,除了日积月累摆放整齐用钱买的新砖外,到处堆放着缺角少豁的砖块,它们是用来铺地,或者合二为一砌墙使用的。还有一些白的灰的大石头,也散落在院子一角,它们是用来下地基的。终于有一天,颓废的土坯围墙被完全推到在地,父亲拿着垂线,亲自上到夹板上砌墙。他很少请工人的,偶尔请一两个帮工,也是在自己技术不行的无奈条件下请的。哥哥是小工,和泥铲灰,母亲和姐姐,会到很近的水井里打水,供应砌墙的需要。
那年父亲不仅改造了围墙的质量,也给小瓦房出了一个檐。顶上披了一块坚实的混凝土雨衣,宽不到两米,但已经很宽阔了,使得原来低矮的小房子气派了很多。晴天,我们坐在檐下晒太阳玩耍;雨天,不用进屋就换好了泥鞋子。父亲建设自己的家,除了必须要买的,从头至尾都在精打细算,无时无刻不再想着节约,所以他尽着自己所有的力量,从10几里之外的煤矿骑自行车赶回,不怕苦不嫌累地亲自干着。
院内已经长了多年的洋槐和泡桐,有腰般粗细,被风吹得飒飒响。父亲要给小瓦房内铺上一层楼板,成为矮阁楼,使它冬暖夏凉,使它不再被老鼠掘洞生子,使它不再落满灰尘,使它能够储存物件,这需要大量的木头,但这是完全买不起的。一直清晰地记得,我们一家人除掉桐树时的情景。完全砍掉大树冠,只剩下一搂粗的干了。父亲和哥哥早已在树根部刨了很深的窝,继而使劲砍凿,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衔接。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我、弟弟一字排开,拽紧很长的绳子,父亲吆喝着“一、二、三”,我们一起使劲,粗重的树干从根部“咔擦”断裂,轰然倒地,大家满头大汗地笑着。没有完,解下绳子再去拉另一棵。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堆满树枝残叶和横亘的大树干。经过电锯厂师傅加工后,父亲利用他的空余时间,对这些木头进行刨光油漆,一块块拼在一起,使得我们的小瓦房更加温暖、干净、舒适、实用。
从堂屋的门口到院门,有一条一米来宽的路,门外种了一行大白杨。接下来的工作,已经完全无需父母动手,我们在院里院外、小路两侧种上各自喜欢、也可能完全叫不出来名字的花花草草。母亲会种一些青菜;哥哥随手一扔是成行的地雷花;姐姐每年都种植凤仙花,她要用白矾砸碎花瓣给我们包红指甲;我会浇水施肥;弟弟会和小猫小狗在期间捉迷藏。在夏季里那阴凉的浓荫下,我们时常打扫、种植,或是采摘、收获。
这纯手工的院子,无论是大人小孩,都积极地参与进来进行有效的劳动。在勤劳的双手下,它逐渐完善,日渐美丽。我时常认为,它就像母亲纯手工压出的红薯面条一般,十分美观,有营养,有滋味。父母似乎从来没有对我们的学习进行过相应的指导和督促,我们在父母对家的改建工作中,都陆续健康地长大了。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土地承包,我们家曾经分得一亩三分地的菜园子。父母姊妹兄弟不分昼夜地勤劳苦干,因为这是改变贫穷面貌的唯一契机。
当夏季以磅礴之势,汹涌而来,我们家的劳作项目也日渐丰富起来。菜地三五天要浇一次水,包菜要打药了,小葱已经长得很高了,可杂草拼命与它争夺土地的营养,西红柿要打叉插杆了,豆角要搭架了,小青菜该上市了,辣椒和茄子也该追肥了……手心里的温柔,手心里的耐心,手心里五彩斑斓、凝重的油画,手心里退却的死皮和僵硬的老茧……换来满目各异的绿呀!西红柿叶子苍翠油亮的绿,小青菜活泼清浅的绿,茄子毛茸茸泛白的绿,线豆角翠色欲滴的绿,包菜硬爽爽的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黄瓜细长鲜嫩,刺儿扎手;西红柿粉红娇艳,汁水四溢;长而弯腰的紫茄子挂在枝头;红的绿的辣椒灯笼般招摇着;包菜已经出售,青菜已经是盘中美味……除了自己家中使用的一些蔬菜,其他绝大部分被送到菜市场出售。
“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就要种白菜。”当夏季那些炫目的蔬菜逐渐退出季节的舞台,腾挪出朴实萝卜和白菜的位置时,已是初秋。
暑假也快要结束了,我们跟着父母在田间劳作。经过火热夏季的蒸腾和消耗,拔掉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棵,土地已经处于疲惫状态,我们开始往土地里追施农家肥了。架子车处于极度忙碌的状态,它不分白天黑夜地运送着。我和弟弟牵着绳,走在前面使劲拽着绳梢,父亲和哥哥各自驾辕拉着一辆架子车,姐姐和母亲在架子车尾巴后推。夕阳西下,奶奶翘首西望,仍不见劳作之人归来。
秋季是播种的季节,也是耕耘的季节。父亲和哥哥用大平耙,耙出一道道宽两尺、厚一尺的梯形小土坝,来种植大白菜。萝卜也是如此,只不过小土坝稍稍小了一点。这样的模式便于浇水,蔬菜能更好地吸收阳光和大地的营养,能更好更快地生长。我们开始下种,两周后剔苗,三周后定苗。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后,当冷霜覆盖地面,萝卜已经碗口那么粗,足足尺长。大白菜瓷实、厚重,绿边白心,一棵10几斤重。外地的大卡车行驶至地边,砍掉、装车、付钱、运走,美丽的秋之收获,如花朵般在全家人的脸上层层绽放。
这样的工作整整持续了6年。年父亲认为他完全有能力进行第二次房子改造:他要推掉已经漏水的小瓦房,盖两层纯砖和混凝土结构的楼房。这次,他请了工人,但是只有大工。他亲自做小工,从土地的丈量到地基挖掘,都一丝不苟,临阵指挥。小型的压土设备,吭哧吭哧地打着夯,父亲吩咐放学的我们干这干那。母亲买菜做饭招呼匠人的用饭、饮水。因为人少,加上收麦、收秋,这两层建筑物耗时一年才趋于完工。我们一家在邻居家的两间小瓦房里居住了一年半的时间,第二年秋天,才搬进新房。在那期间,哥哥和姐姐都成家结了婚。
从没有钱,到有钱,父亲都在至始至终按照他的原则为家庭操劳着。他无声地肩负起沉重的家庭负担,从事煤矿工作和田间劳作,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他抱怨过,喊过一声累。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语言教育的家庭里,不辍的劳作,榜样的力量,就是最科学的素质教育。我们坚强、隐忍、吃苦耐劳,我们沉默、智慧,而又勇往直前。
3不知什么时候,城镇和郊区瞬间刮起造房热。不管是有用无用的房,一律废弃;高的低的楼,统统铲平;国家规划开发的或是私人违法偷偷开发的,都在进行。房地产事业以燎原之势,燃烧至城镇的角角落落,乃至那些臭气熏天、无人问津的水潭泥沟。新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那些仍旧固守着坚定信念的小院土地所有者,被那些开发商的慷慨承诺蛊惑得晕头转向。挤兑得无法不放弃土地的原本的农民,也逐渐一批又一批住进套房,欣欣然数着钞票。大块的绿色土地,一夜之间被圈起,大片的绿色树林被灰色的混凝土建筑代替。被眼前利益所趋,被当前形势所迫,年我家和邻居做了最后的商量,联合开发自家的院子。那时,医院,而且再也没有健康地走出来。
那阔大的有杨树叶子飒飒作响的美丽院落,早已随着父亲渐行渐远,最后消失于我那泪眼蒙眬的视线。而今,我站在曾经的院落,它早已面貌全非。前后皆是6层瓷砖贴就的建筑,高大威武。下面是一排车库,上面是钢筋混凝土的大笼子,结构科学、严谨。小鸟一般的我们宅在简易不需要多多操劳的家里,在互联网上游戏,和陌生的你我说着陌生但似乎熟悉的话语。
满眼的苍白和沉重,到处是静止和孤独。沐浴在迷离的阳光中,我们在无所事事和百无聊赖中品味着百年孤独。展眼再也看不见浓郁的绿和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听不见小鸟清脆的鸣声,闻不到满院杂花的芬芳……大片大片的地方,只有僵立的灰色建筑物。它们既没有城市的科学规划,也没有农村的自然田园,这里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像农村。鳞次栉比的混凝土建筑代替了大自然生动的斑斓,使得柔软、温情的土地变得生硬而冷酷,使人活得自我而不自在。
无数个清晨,推开窗户,仰头看见狭长的天空,俯首是一排整齐有序的各色汽车。那曾经的绿色草坪,或许因为挤没了汽车停靠的地方而被清除殆尽。巨大的小区,没有昂扬大树的青葱挺立,没有河流湖泊的自然绕行,没有假山小兽的优雅游弋,只有那小片的绿色在楼与楼之间的窄小空间喘息。在朦胧的晨光中,唯有静止的汽车色彩妆点着新建的小区。高楼林立,喧闹中的一切更显得格外孤独。
回头看到儿子坐卧于沙发玩手机,爱人在看电视,我们的小家也经常处于这种孤寂和僵硬之中。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基本的劳作,不动手的大脑会变得越来越呆笨。到学校看到四五年级的学生还不会扫地,抹不净一张桌子或者一块玻璃,我的心日渐疼痛。那些我们曾经在《朱子家训》里耳熟能详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这些基本的动作孩子们也不会了,也需要老师布置成特别作业,进行专门的训练。我们失去了大大的院落,失去了参与劳动的大环境,失去了立体、鲜活、磨砺我们性格的家。
社会在滚滚前进,眼前的一切恍然如梦。几十年漫长岁月的变迁,带动住房的发展。我却在祭奠,祭奠父亲,祭奠已失的过去,祭奠那渐渐远去的家。我也渐渐老矣,但我还要双手擎起宝盖头,要使“家”巍巍然屹立于苍穹之下,托起明天依然东升的太阳。
专栏题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漯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河南思客签约书法家潘清江
作者简介沈文兰,女,河南省渑池县曹端小学教师。
本文作者沈文兰授权河南思客独家刊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河南思客
博客/微博/ 委 吕佩义 胡耀桢 王银玲
庄凤娟 刘文玉
统 筹 杨海燕
本期编辑 杨子薇
沈文兰的相关文章●十字绣时代
沈文兰
●有多少爱不要重来
赞赏
人赞赏
北京治白癜风去哪家医院比较好身上有白癜风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