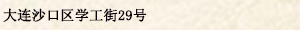吃的重大包菜花生酱及偷情
看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最羡慕的是他自己种菜吃的“耐烦”之心,看他一年的蔬菜收成实在不错,十余种,一家人吃起来是饱足的,他选择居住的汨罗江畔我只是轻浮掠过,印象中没有山,也不知道他定居的山在哪里。只有烟雾一样的绿树,缓慢而沉重的白鹭,将绿树当作背景飞。那条著名的江浅而清,没有烟火气。那里种出来的包菜一定好吃。
有书叫《素菜治百病》,包菜是清肝壮阳的首选菜,我从前只是在红菜汤里爱吃它,软,懒散,上面有点蕃茄造成的红油。浓重的油腻的红房子,悄无人迹的凯司令,那些没落而顽固存在的上海人的西餐厅总有这道菜——真是上海人的。三十多岁满面油哈气的男人,同样苍老却还打扮着的女人,一起倦怠而满足地带着考试成绩不错的女儿去吃饭的地方。不过他们叫罗宋汤,因为是当年的穷白俄瘪三留下来的遗迹——这个城市大概就这么点白俄遗迹了?
上海人管茄子也叫落苏,也怪异得很。
在湖南第一次吃到了手撕包菜,新鲜白亮的绿色,即使到油里火里去走了一回,还不肯掉去——一如湖南女人的性子。配菜的青辣椒也在争宠,包菜是不规则的手撕无误,青椒却是精致的菱形片,带着白色芬芳的筋,几乎每家饭馆都有,也都一样的好吃,手工业时代的操作却有着近乎精美的流水线结果,我想是湖南人摸透了包菜的个性,它需要的就是一点挂在身体上的颜色(酱油给的)、一点味道(辣椒给的)、一点尊重(被漫不经心地撕开总胜于整齐机械地切开)。
湖南的天气真是不好,闷且湿热,北京人这几年爱叫桑拿天,其实他们哪里懂得什么是桑拿天,要过了长江,才能感觉到那种气息——似乎是进了一个阳气暴烈的蒸笼,一切升腾而起,陡然地让人没有了脾气——汗水是把胸背都弄得贴在衣服上为止的,难怪湖南的男人不穿上衣的居多,大街上走着,一两个壮实的乡下少年,黑而粗的脸,蛮横无理地追打在炎热湿润、脏水塘似的街道上,像一个夏天的梦,说不出是美丽抑或是恐怖。
湖南女人蛮横而泼辣,只有她们做得出手撕包菜这种生机勃勃的蔬菜。想起马王堆汉墓的辛追复原像,虽然是美化了很多,但肯定有几分神似,特别是脸上的神色,高颧骨,凌然有杀气——看看他们留下来的绘画就明白了,根本就是非洲岩画。有几分像马蒂斯的后期作品,点滴淌着蜜一样的光泽。
北京的餐馆,稍微正式点的就土,不如街边小店那么由衷粗略地畅快,可是手撕包菜只有这种土气而装潢崭新的地方有——局促的整体气息,从外地学了些菜回来,大概表示自己也能接待四方来客,也是个场面上的地方。其实菜名就表示了他们的虚心——北京人管包菜叫洋白菜。可惜手撕包菜在这里被蹂躏了几遍,首先不是撕开的,是那么简略地排列在盘子里,层层叠叠,洒上些酱醋。因为不会做,唯一的信念就是保持菜的美观,堆在那里缺油少盐的,这道菜简直就是个穿惨白婚纱的新娘尸体,因为惨白,也不算艳尸。
其实北京市井小店的虾皮炒洋白菜一样好吃,两者都有点甜香,配合到一起,不逊于湖南的那道名菜。不要脸的大饭店把这道菜学去,改名虾米包菜。上次去一家号称北京金领店的餐厅,店员劝点的时候,总是说,点吧,家里做不出这味。怎么做不出?谁家没锅没油没虾皮?这道78元的昂贵蔬菜,专门给那些如水泥墙般装潢自己的白骨精吃,倒是相得益彰,她们的胃口和趣味都是改造化的。
花生酱的境遇完全不同。包菜适合粗吃,可是花生酱却适合精细地咀嚼,用花生酱抹面包什么的,或者直接挖花生酱吃,最粗胚了——大概只有剽悍的美国人爱这样。
杜杜说张爱玲意识到吃的严重,在书中往往只有夫妻才能同台吃饭,偷情者的吃都没有好下场——真是聪明的发现,例如王娇蕊,从开始就吃个不停,切下火腿肥的部分给丈夫吃,然后拿着琥珀桃仁卖弄风情,又喊新的潜在勾引者帮她塌花生酱——但是就是没和振保一起吃成饭,塌花生酱的时候也是她自己在吃,可见他们的爱情凶多吉少。电影里的陈冲已经完全没有上海女人味,但是她要振保帮她塌花生酱的时候,还是有种生硬的媚态。
上海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吃花生酱,夏天家家卖蒸制的冷面,上面居然洒的也是稀释的花生酱。第一次吃我完全愣了——在外滩附近的一家小餐馆,估摸不是开给游客的,就是那种少生意的本地人的店,有几个中年人在漠然简单地吃,其实也不难吃,就是平淡一些,很索然,感觉是吃了完全不可吃的东西,例如嚼了报纸,白喇喇地空虚。
冷面实在不是一种美味的食物,但是在上海,这么非理性的饮食之地,一切都昂然下去,弄得我到了北京满街找芝麻酱凉面吃。有次去当年尚未倒闭的北剧场看戏,和一个不太熟悉的女人看戏前随便吃饭,她高个子,有北方女人的快乐和寡淡。犹豫了一下,就把她吃了一半的芝麻酱凉面吃了,面不改色,实在是好久没吃了。她大概觉得我在追求她,也就没说什么。她一直在和人闹恋爱事件——有阵子完全不工作地闹,所以很容易想到那方面去。
上海繁荣的花生酱把芝麻酱排挤得完全没了踪影,要在大超市里才能找到。要么就要在一些古怪的地方才能找到,家人甚至转了两次汽车去康定路一个菜场买。有次从北京坐飞机,随便往包里装了两瓶芝麻酱,安检的时候,那个满脸晦气的女人看着这玩意就生气,但是也没让我开盖检查,大概她也嫌麻烦。我庆幸没有,当时空落落的旅行包,就装了它们和两件白衬衫。
吃真是重大的事情,不过现在过于丰衣足食,没人再那般看重这种仪式,我们往往是和偷情者的吃喝次数多于和名正言顺的那个人。偷情偷得好,吃起来也分外地骁勇——好像莫言写过的爷爷和奶奶最初相识的那几天,在床上的生活——吃都是利用性交间歇,所以吃得快,多,猛烈。偷情不好,当然吃得也索然——大仲马的小说里,火枪手去找吝啬的老情妇借钱,被迫亲热之后,她把一只瘦得皮包骨的母鸡做成汤,然后仅仅撕下一只翅膀给他——这么黑色幽默的饭局,只有老女人和包小情人的老男人才能做到。
新婚夫妇的胖,当然也是性和食物的双重刺激。鲁本斯的画里,人人皆肥,看《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当年欧洲最发达的荷兰是吃的集散地,资产阶级肯定比封建领主吃得少而普通,但是胃口一定更放肆——灵魂自由的缘故。
其实张爱玲也写过非婚者的饭局,《阿小悲秋》里的哥尔达,虽然长得像块半熟牛排,吃起来还是毫不动摇,约女人吃饭总是那么几道菜,对面吃饭的女人全都是鱼水之欢。细想想,年代的上海风流男人还是比我们现代人有礼仪,上床前至少还有顿常规饮食,现在的却是几乎不沾饮食的边,来了就做,做完快走人,成为无数人的原则——哪里还有得吃?大概只有性太满足,期待第二次的,才会鬼祟地笑容满面地去吃。
要么就是凄凉版,找不到性伴侣的老男人为了延迟小伴侣的跑路,请他尽量多吃点,《荒人手记》里写过。
另一场非婚饭局是曼桢和世钧最后的晚餐,前面那么多次同桌都不算,始终有外人,他家或她家的家里人总在旁边,嘈杂的,拥挤的。可以想象张爱玲的婚姻态度——即使两人成亲,大概也还是一样地杂乱,热闹而无趣,是中国古画里的行乐图,看着和实现着,都是乏味而捱时间的,花哨而破败。人最少的时候,他们吃饭也是三个人,小说开始的地方反复出现,证实恋爱期吃不是主调。恋爱中的人大概是饱满的,成天食也不知道味,就算是在厨房中堆满了调味品,真正吃的还是爱人的身体和气息。可是世钧和曼桢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到了真正没干扰的时候,可是这餐饭,已经有“我们回不去了”的招牌在那里,所以吃的什么我们根本无从谈起。
配图取自张爱玲画作
北京白癜风医院咨询北京看白癜风专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