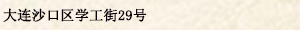马平阿三
“别哭,我最爱的人
今夜我如昙花绽放
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
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
别哭我最爱的人
可知我将不会再醒
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
我的眸是最闪亮的星光
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
这世界我曾经来过
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
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
阿三站在光怪陆离的舞厅中央,哀哀怨怨地唱着自己的心声。一手搂着她的同性恋人,一手握着话筒。我记得是年的夏季。
阿三长得很美,一双水波流转的大眼睛,覆盖着一层上下飞舞的浓密睫毛,身高一米七零,丰满、圆润。多才多艺,一手行云流水的钢笔字落在雪白的纸上,如清丽的蝴蝶安静而美丽;跳得风情婉转的霹雳舞,全县一流;还有她的歌声,沧桑低沉,诉说着青春的故事。当一身黑衣的光头阿三在舞厅出现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引起一阵骚动。
“阿三,起来吃饭了!”她的母亲每一次都会站在她的窗外吆喝着睡梦中的阿三。阿三的确喝多了,她夜夜烂醉,昨晚在东关舞厅,她喝了至少十瓶青岛啤酒。我坐在她的对面,看着一袭黑衣的阿三烂醉如泥。
“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喜欢她呢?她现在不理我了,都怨我,都怨我。”
她再一次掏出女孩子的照片,在掌心里摩挲着。女孩子叫满满。命中缺水,乳名满满。芳龄双十,清秀娇小,麦色皮肤,清汤挂面似的中分长发,穿着九十年代最流行的印花萝卜裤,齐腰的铁锈红茄克,微微一笑,荡起春风无限。
阿三每天去接送她上下班,买上一大包薯片、巧克力、冰糖葫芦之类的零食,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飞鸽自行车,靠在满满的厂子门口,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寻找着满满的倩影,一旦目光触及到满满的脸庞,阿三空洞的眼睛立刻完成月牙,流淌着无限柔情。
“今天中午吃什么?吃米饭吧?我买了好多你爱吃的菜,给你炒手撕包菜、宫保鸡丁吧、再来一个杂菜肉丝汤。”阿三搂起满满的小细腰,贴着满满肉嘟嘟的脸。
阿三总是让满满坐在自行车的前横梁上,载着满满穿越大街小巷,一个长发飞舞,一个潇洒飘逸,卿卿我我的一对佳侣,引来人们的侧目。
得承认,阿三的厨艺的确好,普普通通的一棵大白菜,经她手里翻转之后,酸酸辣辣,让人一顿吃上两碗大米饭。最常见的挂面,经她在锅里一番倒腾,是一盆红红绿绿的炝锅面。我好几次也吃得口水直流。
阿三家的院子又长又宽,院子里还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掩映着青砖碧瓦的上房和厦房,每年五六月份,槐花飘香的季节,她总是把小方桌树下一摆,给自己的小女朋友做饭吃,当然,也有我们这些三三两两来蹭饭的“哥们”。我们一边吃着她烹煎炸炒出来的葱油饼、菜盒子、水煎包、手工发面馍、猪肉炖粉条等等北方美食,一边看她和她的小女友悲欢离合。有时会打起来,有时会摔门而去,有时会甜蜜无限,有时会难舍难分。
雪白芬芳的槐花偶然落在满满的长发上,阿三就无限爱怜的用手捋捋满满的一头秀发,痴痴的看着满满。
有时候阿三出去买菜,会给满满捎回一大串糖葫芦,这是满满最喜欢吃的零食,满满跳起来去抢的时候,阿三和满满就在院子里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震落满地槐花,然后满满会一头扎进阿三的怀里,两个人笑作一团。
清晨的时候,满满坐在院子里,阿三给她洗头,揉搓着满满的满头青丝,阿三会禁不住嗅一嗅她的满头清香,然后用一条雪白的干毛巾吸干水份,看它们在阳光里飞舞。
每一个相爱的画面,都是那么美丽。
“阿三,我得去做美容里,你晚上把饭做做,做好了去车站接你弟弟,他学校放暑假了,五点到渑池火车站,你可别忘了啊!”阿三的妈妈是一位年仿五十但依然香气扑鼻的时髦女人,烫着时下最流行的螺丝卷短发,喷着定型摩斯,乌黑油亮;白胖圆润的脸,一张涂着桃红色唇膏的丰满的嘴唇;大红格子披肩,紧身脚蹬裤裹着她略显肥硕的身材。她一扭一扭走到院里,穿上靠在墙角的一双浅脸羊皮鞋,理理头发,走出门去。
“哦,知道了,你赶紧走吧,走吧。”阿三嘟嘟囔囔地叼起一支烟,“啪”地燃起来,丝丝缕缕的香烟立刻飘满了小小的房间。她的房间里贴满了梅艳芳、张曼玉、钟楚红等港台女星的玉照,一张张流光溢彩,向着她巧笑倩兮。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阿三的吉他弹得特棒,每一次为情所伤的时候,她就怀抱吉他盘腿坐在床上一首接一首唱着港台流行金曲,床前成摞成摞摆满了港台流行歌星的磁带,一台老式录放机,飘着九十年代港台著名歌星童安格、张学友、谭咏麟、刘德华的歌声,美丽的阿三,喜欢穿着她的黑衬衣、牛仔裤,黑衬衣束在裤腰里,外边是一条镶着金属扣的皮带,踏着断断续续的歌声出门,一个跨步骑上她的自行车的瞬间,你还别说,真是挺帅气的。
“姐,姐——”阿三的妹妹哭哭啼啼的推门进来。
“咋啦?咋啦?”阿三弹掉烟头,眯眼看着妹妹。
阿三的妹妹十五六岁,正上初中,和阿三一样美貌,长发扎起一个马尾,瓜子脸,浓眉大眼,皮肤雪白,穿着白底蓝杠的校服,满脸泪痕。
“他们,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给我要钱,还吓唬我,不准说。我给了他们十块钱,呜——”阿三的妹妹哭得抽抽搭搭。
“他妈的,哪个鳖孙,叫啥?”阿三一边拉着妹妹,一边跳下床。
“不认识,不过他们仨人老在我们学校门口转悠。”
一连三天,阿三都猫在县直中学对面的人行道上,跨着自行车,载着小女友满满,叼着烟卷,虎视眈眈地盯住县直中学的大门。
夜色笼罩了静谧的小城,晚自习的钟声响起来了,学生们开始陆陆续续涌出校门。阿三再次点燃一支香烟。
就在这时,从校门东面走来三个吊儿郎当的青年,小西装、喇叭裤、黑墨镜,吹着口哨。
“美妞儿,钱带了没有啊?”其中一个高个子凑近阿三的妹妹,还顺势捏了她脸蛋一把。
“他妈的!”阿三狠狠地摔掉烟头。
“你别动,在这等我。不然很危险。”阿三把手里的自行车靠在树上,同时抚了抚满满的肩膀。
“啪啪!”阿三跨过公路,对着高个子青年就是三个耳光。
其他连个青年迅速围拢过来。
“快走!快走!她是阿三!”两个小青年拉起坐在地上高个子青年,准备快快逃走。
“阿三?阿三怎么啦?她凭什么打我呀?我又没动她妹。”高个子青年爬起来,捂着脸瞪着阿三.
“她就是我亲妹!”阿三一脚飞出去,把高个子青年踹在地上。
“滴滴滴”阿三腰间的bb机响了。
“你等着,等我回个电话收拾你!”
阿三走到旁边的小卖部里拨通了电话。
“阿三,满满呢?人家妈妈找她哩,问到我这了,你俩在一起吗?”
“我有事,就说我俩不在一块!”
阿三折回来,三个青年突然迅速围上来,对着阿三展开攻势。
四个青年人扭作一团,阿三的妹妹吓呆了,满满从对面迅速跑过来,也加入了打斗行列……校门口迅速围了一大群人,一时间,叫骂声、厮打声混乱一团。
夜色陷入沉寂。
阿三的胳膊被划烂了,腿也一瘸一拐的;满满的外衣被扯了一个大口子,阿三的妹妹吓得瑟瑟发抖。
灯光下,阿三叫了一捆啤酒,一杯接一杯喝起来。
满满赶紧买了纱布给她包扎了一下,两个人就这样在酒吧里坐了一夜。
阳光爬满窗棂。阿三一个翻身,看到了身边的满满,恬静的小脸被划了一道,还沾着灰土,睡得又香又甜。她不禁吻了吻她的脸庞。
阿三胳膊的伤口却又疼了起来。
“阿三,咱们去输输液吧,好得快,天气热,害怕感染了。”
“求!感染去求!”阿三一把扯点纱布,坐起来。
“满满!满满!你给我出来!”满满的妈妈急切的拍着阿三家的门!
“我妈?咋办?我一晚上没回去了!”满满侧耳听着门外。
“满满不在这呀!阿姨。”阿三隔着门说。
“开门,你给我开门!你勾引我家闺女!”阿三的妈妈气得开始跺门。
“来来来,你进来找,进来找。”阿三把门打开了。
“你这个死闺女,昨晚都有看见你和阿三在一块,你两天不上班,就在这厮混呀!工资哩?你的工资哩?”满满妈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寻找着满满。
满满却早已顺着院子里厕所的后门溜走了。
“警告你!以后不许纠缠满满!”满满妈骂骂骂咧咧地走了。
病房里。
受伤的阿三躺在床上,满满给她端茶端水,端饭喂药,一瓶青霉素液体滴答滴答记录着无聊的时间。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百无聊赖的阿三在病房里不禁唱起歌来。
“别唱了,我给你按摩按摩腿吧。”满满搬个小凳子坐到阿三床边。
“满满,你对我真亲。”阿三拉起满满的手。
“一会我给你买好饭我得回家转一圈,我妈这两天心脏不好,我得回去看看。”
“好吧,那你快点回来啊,我会想你的。”
“唉,我爸天天不见人影。带个女的满街窜,我妈一个人,挺可怜的。”
“可怜?她天天也不管你,就知道要你的工资去打牌,有啥可怜的。”阿三愤愤不平。
“我这还有八百,我给你交了三百块医药费,剩下的回去先给她吧,只要她开心就行,我也没时间照顾她,她毕竟是我妈。”
“哪有这种妈,坐在牌场上不着家。哪有这种爸,一天到晚就知道泡女人。”
“我哥对我总是不赖呀!”
“也是,你还有个哥。有了你哥,你在家里呀就是个多余的人。”阿三爱怜的摸了摸满满的头。
“那你躺会,我下去给你买份炒面我就回了啊!”
……
满满的母亲瘦弱憔悴,一年到头泡在牌场里,要么就是捂着胸口躺在病床上哼哼。按说满满是她唯一的女儿,可是重男轻女的她把女儿养的仇人似的,见面就骂,抬手就打,满满刚刚比案板高的时候就被调教着站在小板凳上给全家做饭,擀面条,蒸馒头,这使得貌似柔弱的满满性格里充满了叛逆和不屑。别人的妈妈天天接送在校门口,可是满满总是顶风冒雨往家回;别人的孩子年年有新衣,满满却总是拾着表姐的旧衣穿;小时候,满满最羡慕别的爸爸把孩子高高架在脖子上,可是满满的爸爸见了满满总是黑着脸。满满从小在老街上摸爬滚打长大,这家混顿饭,那家睡一宿。一来二去就混熟了老街上的名角儿,什么小四、五哥、赖毛……阿三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在老街上蹿大的孩子,性格里充满了好斗和不安,一群小流氓欺负满满的时候,阿三冲上去就是一顿毒打,从此,满满对阿三充满了感激;阿三也渐渐喜欢了满满,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共同经历着人生的风风雨雨。
几天不见,阿三挺想满满的。她到街上服装店专门为满满挑选了一套藕荷色套裙,来到满满的厂门口。
满满一出现,俩人立刻挽着手,双双把家还。
阿三炒了四个小菜,撬开一瓶白酒,两个人坐在槐树下,开始对饮。
“阿三!你这个死货!”阿三的父亲醉醺醺的推门进来,对着阿三就是一顿臭骂。
“给我倒杯水!再给我烧盆洗澡水!”阿三父亲是个酒鬼,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泡在酒精里。
阿三起身给父亲倒了一杯水放在桌子上。
“把水递过来!”阿三的父亲一头倒在床上。
等阿三把水递给他的时候,他却把一只鞋褪掉踢得老远。
阿三的妈妈推门进来,刚刚做过美容的脸光滑白嫩,闪着光泽。
“死鬼,你咋不死哩,又去喝酒!喝喝喝,喝死你!”
“我就是喝了咋地?我就是喝了!你这个贱货,你少管我!”
“你才是贱货!你这个猪!”
“你才是猪!”
阿三的父亲突然跳起来,揪住阿三母亲的头发,两个人厮打起来。一番争斗,在阿三的愤然离去中渐渐趋于平静。
这是阿三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
醉醺醺的父亲,花枝招展的母亲,然后是两个人的吵吵闹闹,在她二十年的生命里错综交织,构成她人生的底色。
每一次父亲和母亲厮打的时候,她和弟弟妹妹总是缩在墙角,惊恐的看着他们的剧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
她只有满满。这个二十岁的小女孩,在她那里,她才可以找到一些平静和温暖。她的麦色的笑脸,是她心底最温暖的一缕阳光。更多的时候,他俩喜欢窝在阿三的小屋里,唱歌、喝酒、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消磨一天又一天的时光。
满满被她的妈妈锁起来了。
阿三开始求着我们这些朋友去给满满送好吃的,火腿、苹果、薯片、草莓……
等到满满被放出来的时候,她们俩又如胶似漆了。
秋天来了,舞厅和酒吧再度热闹起来。
阿三继续带着满满坐在迷离的灯光里喝酒、划拳、唱歌、谈情说爱。二十岁的满满依偎着阿三,满脸幸福。
那天夜里十二点,阿三搂着满满唱着“女人花开放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我渴望有一双温柔手,……”
酒吧里突然飘进一阵寒风。
“阿三!阿三!快快!你父亲出事了!”一个中年妇女急急慌慌叫喊着跑进来。
“他?他能出什么事?酒鬼!”阿三继续唱歌。
“真的出事了!医院抢救呢!”中年妇女急得跺着脚。
阿三扔掉话筒,拉起满满就向外跑。
父亲已经不在了。
确切地说是喝酒喝死的。
阿三茫然的站着,看着依然花枝招展的母亲抹着眼泪。看着白色被单下再也不会醒来的父亲。
弯弯曲曲的送葬队伍沿着崎岖的山道缓缓向前,像阿三来不及品味的青春。
父亲不在了,母亲回来的更少了。依然花枝招展,穿过渑池的大街小巷。
每一次我在电话里告诉妈妈中午我想吃的美味的时候,阿三总是那一句话:“这么大了还叫妈妈,看把你幸福的。”
诺大的院子里少了父亲的酒气、母亲的香气,便只剩下两个弟弟妹妹需要照顾。阿三开始断断续续做点小生意,有时倒卖钢材,有时倒卖香烟。然后挥霍一阵子,给弟弟存点钱,给妹妹交交学费,继续在县城里唱歌、喝酒、跳舞、恋爱。没有职业的她成了渑池大街小巷一道独特的风景。我们都会隔三差五去他的小屋里听她唱歌,和她喝酒,聊天。她就把自己的拿手菜一样一样端上桌,看着我们饕餮。
有时她还会拿着酒到我办公室找我,诉说诉说她的心事,搞的全单位的人都来问我:“她是男的女的?找你干什么?”
认识了阿三。我的日子也不得安宁。
一大早,我正在办公室打扫卫生,电话铃声响了……
“安安,我心里可难受,她妈妈不让她出来,可是我想她呀!给她打传呼,她也不回,肯定是她妈妈把她锁起来了,你有空没?我心里可难过,就想找人说说话。”
涧河岸边,初秋的风已有凉意。阿三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头发凌乱,目光呆滞,见了我,就开始絮絮叨叨说她的情事,她的满满,半瓶白酒,随着她的诉说渐渐变成一个空瓶子,又被她狠狠地摔向远处,发出刺耳的破碎声……河水哗哗地流淌,无视人间悲喜。
“不喝了,阿三,满满总会出来上班的,上班了你再找她也不迟嘛。”
“她好像不喜欢我了,我爱她爱了三年,把心都掏出来了,她现在不想理我了。”阿三一把鼻涕一把泪,想着她平时潇洒抽烟的样子,看她那不争气的样子,我感到有些厌恶。
“你都是成人了,怎么这么脆弱哩?感情感情,你一辈子就只有谈恋爱一件事呀?你无聊不无聊。”我真是急死了,一个上午班也没上成,就听她在那里无病呻吟。
“那你……走吧,我们不再是……朋友。我给你添……添麻烦了。你们都烦我,我就去死吧。”阿三摇摇晃晃站起来,走向浪花涌动的河流。
天哪!以她的性格真的有可能自杀。我赶紧一把扯住她:“别别别,我今天不上班了,今天上午就陪你,听你诉苦中不中?”我急得团团转,还得耐心的守着她。阿三真的也挺可怜的,父母不管,她还要招呼着一家人,唉,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呀!
“我真哩可欣赏你,安安,你的画我最喜欢。咱俩坐在我的小屋里谈天说地多美呀!我的朋友里,他们是酒肉朋友,你才是真朋友。”
想想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每天早上阿三到街上喝胡辣汤的时候,总爱给我捎一袋子我爱吃的牛肉煎包。第一个男朋友欺负我的时候,也是阿三出面把他狠狠的揍了一顿才解了我的气。算了,阿三虽有些无聊和无赖,但也有可爱的地方,我还是不能不管她呀!
在清冷的秋天的河畔,我和阿三就那样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坐了一个上午,让自己单纯快乐的青春在她的故事里成熟发酵。
过了这个年头,我二十岁,阿三二十五岁。她的小女友满满也二十三岁了。
那是年的第一场雪。
红泥小火炉,红酥手,黄藤酒,随着洋洋洒洒的雪花和阿三的吉他与歌声在阿三的小屋里回旋缠绕,炉火很旺,四五个盛满白酒的玻璃杯晶莹剔透,在这个寒冷的雪天充满了无名的诱惑。
“干!”
“干!”
“干!”
……
一群豆蔻年华的年轻人,在阿三的小屋里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之后是谈天说地、海阔天空、酩酊大醉。阿三的小屋里不乏帅男,也总有美女出入,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都喜欢和独具魅力的阿三聊聊天、说说话,听她唱唱歌,看她练练字,酒酣耳热之际,欣赏她潇洒的舞姿。看她在雪白的纸上写下徐志摩的“你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我的波心……”,和她谈雪莱、米开朗基罗、夏加尔……
“阿三!阿三!阿三!快开门!快开门!……”在我们几个人迷迷糊糊的睡意里,阿三家的门被撞开了。
“你妈都死了!你还在这里鬼混!”满满的小舅拉起醉意朦胧的满满,夺门而出。
满满的妈妈真的死了。
当我们第二天从睡梦中醒来,看到一身缟素的美丽的满满时,她哭倒在母亲的棺木前,昏过去又醒过来,拼命捶打着自己的胸部。
“妈呀!都怨我呀!我没有好好陪着你呀!要是我在你身边,你说啥也不会走呀!妈呀!”满满昏死过去,阿三赶紧跑上去想抱起她,却被满满的舅舅一把推开了:“去你的,滚!没你的事!”
满满的父亲和另外的女人刚刚生了孩子,闹得满城风雨,满满的妈妈拼了命的去女人家里闹,和坐着月子的女人扭作一团,在地上打滚,却被满满的父亲一把揪起来扔出门去。自此回到家里一病不起。
最后的那天夜里,她想到了满满,想想满满这二十年来和自己相依为命,赚了钱由着自己随便花,不禁落下两行清泪。她走得很安详,当满满的舅舅抓好草药回来的时候,她竟在睡梦中去了。
一向飞扬跋扈的阿三默默的退到人群后边,看着满满的舅舅掐着满满的人中,满眼心疼。
雪,覆盖了尘土飞扬的小城。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没有满满的日子,阿三总是自己在小屋里唱歌。一首又一首,歌唱着自己多愁善感的青春。
阿三很久不去酒吧了。
满满也很久不到阿三的小屋里去了。
新年,在大家彼此安生的日子里过得祥和安静也有些寂寥。
我按部就班的上班,开始忙忙碌碌地评职称、写论文、拍作品,……
“安安,满满要结婚了!你知道不?”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阿三的电话。竟然是一个意外的消息。
满满真的要结婚了。
阿三把一沓折得整整齐齐的信摆在我的面前。
密密麻麻的十几页白纸上,是满满断断续续的忏悔和未曾干去的泪痕。我只记住了其中一句话:“再见了,阿三!我害死了我妈。我不能再这麽混下去了。”
满满妈满世界寻找满满的一幕幕再度涌上我的记忆,她的有着心脏病的妈妈,终于未能看到女儿出嫁。
“我想我一定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阿三半梦半醒地站在午夜里有些寂寥的舞厅中央,唱着《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
阿三终于在满满家门口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满满,只是,满满的身旁,多了一个挺帅气的男人。
“他谁?你说,他谁?”阿三醋意大发,居然失控地揪住男人的衣领子,男人“啪”地一下子打落了阿三的手。
“他妈的!谁让你勾引满满的?谁让你勾引满满的?!”阿三再一次揪住了男人的衣领子。
“咋?想和我斗?你是男人吗!你明明就是个闺女嘛!”男人斜着眼嘲讽地看着满满。
“我就是要和你斗!就是要斗怎么啦?满满是我的!是我的!”阿三涨红了脸,把男人的衣服揪得更紧了……两个人厮打起来,引来一群路人的叽叽喳喳,满满捂起耳朵,转身跑开了。
昏黄的灯光下,阿三的右臂被结结实实包扎了起来,她显然不是男人的对手。
阿三和满满就这样分开了……
“我还是走吧!我准备去武汉,到那里闯一闯,赚点钱,还有弟弟妹妹需要资助。我妈也老了,家里总得有人养活。”阿三在醉了一夜之后,对我说道。
“也好,你都二十五六了,该干点正事了。”我说。
阿三的弟弟刚上大学,妹妹还在高中。而她貌美如花的母亲,因为找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相好,在如火如荼的爱情里几乎甚少回家。
“我也陪你去吧。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和我媳妇离婚跟你走,你信不信?”那个叫小猴的青梅竹马的玩伴,对阿三痴情了十几年,也未能获得阿三芳心半寸。
“阿三,不是我吹牛,你只要答应,咱俩现在就结婚!”从小跟在阿三屁股后头长大的小摸斩钉截铁地发誓。阿三也不肯正眼看他一下。
阿三走后的第二年,我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看到长发飘逸的满满抱着襁褓中的儿子,拽着丈夫的胳膊,神气十足的走过街头。她是幸福的,至少,比在阿三的小屋里幸福。
我也结婚了,妈妈也不让我再和阿三来往。
可是有一天,当我走到单位门口的时候。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一把拉住我,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安安,是我呀!”
阿三!
一晃都四五年了,阿三又回来了?
“走,我请你喝胡辣汤。”
“还是我请你吧。”看着阿三落魄的样子,我挺可怜她的。
在仰韶大厦拐角的那间熟悉的早餐店里,我和阿三边喝边聊。
阿三真的变丑了,黑、胖、被香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毛孔粗大的脸,她的美貌被她非正常的生活摧残得面目全非。
“我可是辉煌过。”
哦,阿三真的辉煌过。
她在武汉无论做着什么生意,反正拥有了轿车、女友、名贵的香烟、夜夜笙歌,并且一掷千金。
“我一晚上赢几十万你信不信?”阿三赌博。坐在金碧辉煌的赌馆里,或者偏远破旧的破房子里,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赌徒挥金如土,她的身旁,坐着她宠爱的吸金女友,淹没在乌烟瘴气的一堆男人里,金黄的头发干枯散乱,滴血的口红咄咄逼人.她们夜里交织在一起,白天就开着车在武汉城里转悠,所有的一线品牌、金银首饰、山珍海味全部尝试。
天哪!对我这个上班不久的老实巴交的小职员来说,一个月工资当时才四百多。
“不过,我又赌光了!看我现在。”阿三苦涩的一笑。
在她和武汉女友缱绻缠绵的那个夜晚,女友在她酩酊大醉之后,席卷了阿三身上最后一张存折,把仅剩的十五万洗劫一空,绝尘而去,查无消息。
“千金散尽还复来。”我逗她。
“来不了了,真的来不了了。我这辈子算是毁在女人手里了。”阿三这么说着的时候,眼神茫然。
听说阿三又喜欢上了小城的一个少妇,离婚,多金。
阿三又在舞厅里出现了,带着她的新女友。
新女友纤细、优雅、精干。是一家公司的会计。
她们紧紧拥抱,唱着柔性蜜意的情歌。
“你是我的情人,玫瑰花一样的女人……”是刀郎的歌,阿三唱的真好!舞厅里阵阵喝彩。
多金的新女友,因为生育了两个女孩,一心传宗接代的土豪丈夫就开始看她不顺眼,隔三岔五没事找事,先是恶语相加,几个月后看看媳妇的肚子还是没动静,就开始家庭暴力,丈夫喝得醉醺醺的到单位滋事,阿三出面保护,把那男的打得头破血流。
从此,阿三和这个叫慧的女子租房同居在一起。
“真的有意思吗?你和猴子结婚算了,他那么喜欢你。”我说。
“我不喜欢男人,看到他们就讨厌!我爸、满满她爸,不都是酒鬼!还打媳妇!还有慧她丈夫,有一个好的吗?”阿三摇摇头。
既然她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总有自己的理由吧,我应该祝福她。
阿三又开始每天买菜、回家做饭、等着慧下班回家。
“慧跟着我可幸福呢!她是我爱人,我每天会在家里做好她爱吃的饭等她回来。”阿三真的是一脸幸福。
阿三断断续续倒卖一些香烟,顾着生活的花销,她还攒些钱,给慧买一些慧喜欢的首饰衣服什么的,这样也挺好。
可是有一天半夜,很久不联系的阿三突然给我打“安安,快借我五百块钱,我的房子漏雨了,我暂时没钱,我不想花她的钱,她也不容易。”
唉,我只有从自己紧紧巴巴的工资里给了她伍佰元。
上班、家务、孩子,我和阿三不再是以前坐在涧河边饮酒的小青年了,日子匆匆忙忙,抹去了许多放纵的青春。
“安安,咱俩合伙做生意吧?去山西贩煤,你只用入股就行了,我来操作,肯定赚钱。”
贩煤?对我来说很是天方夜谈。
“我现在资金也不够,就当你帮我吧,赚了按比例给你分成。”
说实在的,就阿三那颠沛流离的状态,我咋敢入股呢?!
一连几天,阿三都到我家里来,有时给儿子买一大包零食,有时拎着酒和小菜。坐、拍、还主动给我做干煸牛肉。
唉,就当我帮忙吧,我把自己卡上的五千块给了她。说实在的,我心里没底。但是看到可怜兮兮的阿三,我又无法拒绝。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过去了。
我没有见到阿三,她也没有联系我。
只是听朋友们断断续续讲了她的故事。
做了几笔烟草生意赚了几笔大钱,又到赌场挥霍一空。
又做服装生意、白酒生意,兜兜转转,没有存住几个钱。
慧和她分手了,因为阿三太穷,纯粹吃她的软饭。
分手的时候,慧给她要五千元青春损失费。
不是我那五千元吧?我心里真的不敢保证。
我想起了满满那纯真无邪的笑脸。
春天来了,阿三家院子里的槐树又开始抽枝发芽,阿三风韵犹存的母亲穿着大红的旗袍,将染过的乌发高高挽起,准备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阿三站在母亲背后里发呆,把吸了一半的烟狠狠弹到墙角里去。
“阿三,看我的头发后头乱不乱?”阿三的母亲一边喜气洋洋地看着镜子里浓妆艳抹的自己,一边招呼阿三再为她拾掇拾掇。阿三捡起一枚小黑发夹,把她脖子后头的一缕头发别上去。
鞭炮劈劈啪啪的响起来,唢呐嘹亮地吹起来,阿三的母亲撩起旗袍的一角,坐进白色的轿车里去.........
天上的云又高又白,阿三看着一瞬间散去的人群和门前鞭炮的碎屑,感到无比孤单。她拿起桌子上喝了半瓶的白酒,咕嘟嘟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弟弟在远方有了自己的家;
妹妹明年也要结婚了;
空旷的院子里,满满坐过的那把小竹椅落满了灰尘,阿三的影子被黄昏的夕阳渐渐淹没。
......
转眼之间,时间就过去了整整十年。
有一天,我接到了阿三的电话。
“安安,欠你的钱我一直没还,真的不好意思。我现在真是没钱,你能再借我点吗?两千,两千就行。”
沉默。我最终没有答应。
因为,我知道,阿三开始吸毒了……
当我们在结婚生子、上班下班的忙碌中渐渐淡忘她的时候,一直单身的同性恋的阿三开始和小城里一群吸毒者聚在一起吞云吐雾。
在那间密闭黑暗的小屋里,清晨的一缕阳光照在阿三蜡黄的脸上,她的身旁,歪歪扭扭依靠着和她一起吸毒的同伴。
阿三断断续续给我打过几个电话,让我再资助她一些钱。我没敢答应。
当我偶尔看到她骑着她那辆旧摩托车穿过渑池的大街小巷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有意避着她。有些拯救注定永远是徒劳。
时光早就埋葬了她和满满的爱情。
现实也早就粉碎了她关于生活的梦想。
而满满,却注定是她心上的一颗朱砂,在岁月的百转千回里,留下若有若无的疼痛。
……
年,小城里发生了离奇的凶杀案。死者身中七刀,刀刀都是要害。死者是满满的丈夫。
披头散发的满满披麻戴孝,时哭时笑。
大家都知道,满满的丈夫自从开了煤矿鼓起了腰包,便弃满满于不顾,在外花天酒地,喝完酒回去就打满满,遍体鳞伤又生性倔强的满满拥着两个可爱的孩子,至死不肯吐出“离婚”二字。直到那一天,醉醺醺的丈夫把病中的满满打得昏死过去。
第二天,人们在满满的卧室里发现了满身是血的丈夫,双目圆睁,欲语还休。
满满的家门口围满了街坊邻居,一边叹气一边搀扶着声音嘶哑的满满。
阿三也去了,在人群外边,她冷冷的看着警察在那里验尸、测量、记录,表情木然;她默默地看着柔弱的满满,默不作声转身离去。
年,那真的是年的第一场雪,大街小巷是刀郎的《年的第一场雪》,沧桑、悲凉、经典、怀旧,随着翻卷飞扬的雪花渐行渐远……
那个曾经风光无限、风华绝代的阿三静静地走了。
在那间阿三吞云吐雾的破旧的小屋里,阿三的口袋里还剩半包白粉。她瘦骨嶙峋、面色发青,穿着那件墨绿色的男士外套。
她的花枝招展的母亲哭倒在她的尸体旁,哭声中带着谩骂
“你个死闺女,你说走就走了!以后谁管我呀!谁给我养老呀!你个没良心的死闺女呀!”
阿三漂亮的妹妹跪在那里,雨打梨花的样子。
阿三唯一的弟弟也从外地回来了,西装革履,神情严肃,呆呆的站着,似有所思。
白色的纸扎的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我想起阿三家院子里的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树下,曾经留下多少欢声笑语呀!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世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地胶着,想是人世间的错,或全是流传的因果,终生的所有也不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是罗大佑的《滚滚红尘》,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响彻小城......
……
阳光灿烂,鲜花簇拥的广场上,人们三三两两在温暖的阳光里奔跑嬉戏,母亲带着孩子,情侣相拥相携,老人们在悠闲安静的散步,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马平,女,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渑池县美术家协会主席。曾出版诗画集《天使来访》、散文诗画集《马平自选集》、文集《马平抱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