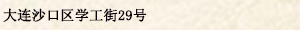中国享受到优死的人,不足1
当生命品质发生无可逆转的退化时,这个社会仍然能够给予临终者免于痛苦和恐惧的可能性,临终关怀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能给他的成员提供的最好的保障。
一
郑丽珠家的大门上方不显眼处贴着一张观音菩萨的画像,很旧很破了,下午时候屋子里光线不好,这个菩萨要仔细看才能看见。然而对于一个癌症晚期患者而言,这个菩萨,或许也意义不大了。
郑丽珠的丈夫李财富不肯让自己请来的医生曹伟华进门,他希望医生告诉妻子她只是得了普通胃炎,而不是晚期胃癌。医生拒绝了,她可以不用明说是胃癌,但不能撒谎说是胃炎。
半个月之前,李财富来到汕大大医院宁养院找到曹伟华,申请希望得到宁养院的帮助。
这是中国第一家为贫困的癌症晚期患者提供免费姑息治疗(亦称舒缓治疗)服务的机构。在香港,李嘉诚看见自己的好友在临终时,即便拥有很好的经济条件,也难免死亡前的痛苦。那贫困的人该怎么办呢?
从年开始,曹伟华就在这里工作,现在她是这里的主任。和每一个从事姑息治疗的工作人员一样,曹伟华和她的同事们,无法改变死亡的牌局,但试图改变死亡的体验。
李财富家是一栋典型的潮汕农村的二层小楼,屋顶用钢板搭成,下雨的时候,屋顶总是滴滴答答响。房间里有一点点简单的家具。
争执一番之后,曹伟华还是走了进去,轻轻地拥抱了一下郑丽珠。
郑丽珠躺在床上,因为太瘦,肋间的骨头高高隆起,里面还有一个刚放进去的支架。曹伟华用手轻触她,她的表情比之前舒展了一些,似乎曹伟华获得了她的信任。
郑丽珠曾经服用过弱阿片类的止痛药,没什么效果,为此,曹伟华需要根据她的情况为她开新的止痛药。
护士李瑞娜也跟进来了。她观察房间的格局,看到郑丽珠的柜子上摆着肠内营养粉,她告诉郑丽珠这个应该怎么吃,告诉她垃圾桶最好不要放在头边。郑丽珠的床离厕所大概有5米远的距离,要穿过客厅,李瑞娜提醒她,晚上尽量少自己起夜上厕所,摔倒了会很麻烦,「那样你会很辛苦,你先生也会很辛苦」。郑丽珠望着她,此时眼神像一只无辜的兔子,连连说「好、好」,她想起儿子说过的:「你们身体没事,就是帮我们挣钱了」。
对于癌症晚期患者而言,身体损坏部分的脆弱超出想象。
「明明是乳腺癌,我已经把乳房切了,为什么到后来走起路来髋骨都会疼呢」,一位患者这么问过李瑞娜,她的丈夫把她从床上背下来,和上一次见面比起来,她的疼痛症状好了很多,但癌细胞的转移并没有因此留情一点。
李瑞娜向她解释说,原来的病灶影响了骨头,并告诉她什么样的坐姿是有利于保护她那脆弱的髋骨的,不要翘二郎腿,也不要把两只脚交叉缠绕在一起。
李财富和社工许乃深在客厅聊天,这是对这个家庭的第一次造访,许乃深需要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广州工作,儿子还没结婚,女儿有一个孩子,许乃深边听边画出他们的家庭树,标注出谁是患者的主要照料者。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潮汕农村家庭,生活节俭,会培养小孩,老两口守在房子里,性格互补,丈夫是妻子的主要照顾者,两人对疾病和健康几乎一无所知。
郑丽珠要面对自己身体无法预知的变化,不断增多的需求。她不知道自己是癌症,但她知道自己状况不好,肿瘤医生不给她进行手术,给她开了一个靶向药,阿帕替尼,没什么效果,但一家人都觉得这个靶向药是一个希望。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了解情况,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人在身边,会舒心多了。
因为对疾病所知甚少而饱受痛苦的人很多。曹伟华见过满身黢黑的病人,一查看他的中药处方,才知道处方里有一味含铅量超标的中草药。也遇见过病人身上的恶性伤口,家人拿洗米的潲水给他敷,混合着发馊的酸味,最终成为一个细菌培养皿,臭得小孩都不敢靠近,伤口本身的感染也越来越厉害。
在晚期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光里,这些痛苦关乎着生命的尊严。
曹伟华接到过一个情况很不好的患者家属申请。他们去到家里,病人卧床,腹部缠着纱布,意识模糊,无法进行语言表达,看起来剩下的时间不长。曹伟华例行为他检查身体,这位病人血压不高,心率不好,因为意识模糊,疼痛感不是很强烈,但曹伟华发现他身体特别脏、特别臭。等到护士李文苑要为患者身体做评估时,曹伟华观察到她在掀开病人衣服之后,愣了一下,立刻转过头,对病人家属说:「你们弄两盆温水来」。
李文苑转身拿出工具包里的一大堆清洁敷料,戴了两层口罩,回到病人身边,这是一个做了造瘘手术的病人,家人不会护理,医院给的肛袋也没用,回到家的三天时间里,病人躺在床上,粪液从腹部一直流到颈部,枕头以下,曹伟华向我形容说,整个人泡在粪水里。那整个下午,她都觉得这股味道一直跟着她。
李文苑花了半个小时为他清理,整个过程中,病人虽然不能说话,但一直高度配合李文苑的动作要求,面部表情逐渐舒展开来。李文苑又让家属到附近的市场买新的睡衣和床单,为病人换上,并教会家属如何为病人进行护理。
不到48小时,这位病人的女儿就又再次来到宁养院,退还多余的纱布和肛袋,并告诉曹伟华,父亲已经去世了。最后48小时,父亲干净、清爽,穿着干净衣服,就像睡着了一样,他们感到很安慰。
二
当初曹伟华从内科转到宁养院的时候,旁人和她自己都有过一些疑惑。她的医学晋升路一直很顺利,病房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有成就感的地方,作为医生,你在努力和疾病抗争,感受现代医学为人类生命带来的「无限」可能。
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人类的死亡往往离奇又充满诗意,年,伦敦的一位男装店店主发布了第一份死亡量化纪录,那时候,人们死于「无疾而终」,死于「忧伤」,还有人死于「昏睡」。
是现代医学改变了这种语焉不详的死亡体验,20世纪以后,医院、死在病床上,死于某种被命名过的疾病,死亡纪录不再诗意,变成了冰冷又程式化的医疗体验。
到年,人类三分之二的死亡都伴随着慢性疾病,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这三分之二的人都要面对自己身体或快或慢的衰竭过程。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医院经历过不惜一切的治疗,他们被送进ICU、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做了一场大型手术、离开的时候身体还被输着抗癌药。
《最好的告别》中提到一位癌症晚期病人,「永久性器官造口术、鼻饲管、透析导管插满了她的全身,她躺在哪里,身体连接着这些泵,时而清醒,时而昏迷。」
这种「生命不息,抗争不止」的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赋予了人类反抗自身局限性的种种力量,它反抗过基因、血肉、细胞、骨骼,保证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帮人延缓死亡。但这种精神并没有帮人更好地思考死亡。
对死亡的避而不谈,往往给人带来不好的死亡体验,这种体验里掺杂着遗憾、绝望和过度治疗给患者带来的肉体痛苦,对于活着的患者家属而言,这种痛苦更放大了他们的无能为力,虽然他们那么尽力想要避免自己所爱之人的死亡。
将死的人想要什么?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描述过这样一个人在临死之前因得不到任何同情与安慰而痛苦的故事。那是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伊万·伊里奇在临死前渴望(虽然羞于承认)的不过就是:「有人能够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地同情他。他渴望得到宠爱和安慰。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务员,胡须都白了,所以,他知道他的渴望是徒劳的。然而,他仍然这样渴望着。」
然而,死亡是一个比现代医学存在时间更长的事物,人类都知道生命有尽头,死亡却仍然在大多数文化中成为禁忌。在中国,科学唯物主义近几十年的发展,更是让人们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认为什么都是不真实的,人们以「英雄」的姿态与死亡抗争,在生命尽头仍然不停止向身体内打进抗癌药,在最后一刻,选择让自身被狠狠摔向死亡,「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
如果医学无法改变死亡的结局,是不是意味着医学的无能?
还是医学生的时候,曹伟华就意识到医学有它的局限性,「我们已经尽力了」这句话只能带给患者和家属绝望。「那我为什么不去想办法让他在生的时候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他能够活得更有尊严,能够把自己能安排的事情安排好」,曹伟华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姑息治疗,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HospiceUK的临终关怀院全国主管RosTaylor说:「让死亡变得更美好是很简单的。重要的是关于良好疼痛控制的基础知识以及和人们谈论重要事务,这可以让死亡的过程发生很大转变。」
曹伟华到宁养院工作时,熟悉她的人可惜她的专业能力,她是一个优秀的、前途无量的内科医生,而宁养院的工作看起来就是开开止痛药。姑息治疗最重要的不是昂贵的技术和药物,医院里,也算是个赔钱的科室。年轻医生总是来了很快就走,既辛苦,成就感也不高。
不熟悉曹伟华的人则质疑她是不是专业能力不够所以被派到宁养院,曹伟华懒得去争辩,她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对她而言,宁养院的工作和内科医生的工作一样有它的价值。
有时候给患者带来希望和舒适的就是每天90毫克的吗啡,而不是靶向药。
三
李泽钦是曹伟华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位病人。
他住在汕头郊外的一栋二层小楼里,这是父母留给他的房子,一楼他用来做木工,当然,仅限于他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穿着背心做一条小椅子,汕头的秋天依然炎热,他比之前胖一些了,状况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工作两个小时。
经过一个陡峭的木制楼梯上去,二楼就是他和妻子的住所,一个观音菩萨的神台摆在楼梯口,老式的潮汕家具都由李泽钦亲手制作,就连这个陡峭的楼梯,也是他30多岁时自己做的。年,李泽钦被诊断为鼻咽癌晚期,这是一种在广东地区比较高发的癌症。他问医生,还能不能看见北京奥运会,医生说:「可能看不见啊。」
年,李泽钦找到宁养院,他刚结束放疗,出现大出血,他的想法是,死的时候不要那么痛吧。那时候曹伟华也觉得,他可能超不过半年时间了。后来李泽钦没想到自己看见了奥运会,又看见了女儿结婚,还等到了小外孙女的到来。
每天晚上,李泽钦都去旁边的光华路走一走,但因为还算年轻,他不敢用拐杖,只敢假装推着一个自行车支撑自己。李泽钦的妻子因为身体不好,十几年来医院,只能在家做手工,每天挣十几块钱来支持家用。从被诊断为癌症,到治疗,到后来找到宁养院,李泽钦每周都自己去宁养院拿药,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病人的样子,忍着疼痛,双腿无力,呼吸困难,「兄弟姐妹都讨厌我,别人问起他们,我就说他们都很忙」。
即便从死亡的威胁中暂时逃脱出来,疾病仍然困扰着李泽钦,他的左眼已经近乎失明,左耳听力也逐渐退化,和从前的痛苦相比,这不算很大的困扰,他甚至觉得,自己做木工活的时候本来就要闭上左眼,这一切都恰到好处地让他知足。
在曹伟华的经验里,有少部分患者因为舒缓治疗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李泽钦目前唯一的治疗就是止痛药和通便药,暂时没有出现癌症转移或复发的表现。
宁养院一直免费为他提供,维持稳定的药量,定期去家里看望他,了解情况。
按宁养院管理指引,李泽钦应该可以退出服务,但如果停止使用止痛药,疼痛仍然会折磨他,甚至再次威胁他的生命,曹伟华有些矛盾,但无论如何不会放弃他。对于李泽钦来说,宁养院是比他的兄弟姐妹更重要的存在。
曹伟华和许乃深有一个共识,宁养服务,最重要的是发现对方的需要,你再去为他提供这个需要。
许乃深是一位经验丰富又敏感的社工师,脸部线条柔和,话不多,但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两年前,他还在从事行政工作。两年之后,每走进一个患者家里,许乃深就知道,他或许又走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
有时候他会先观察患者家里是否有十字架,佛堂,或者是否有在拜什么神,如果碰到家里有比较明显宗教信仰的,许乃深会问这个信仰有没有为你面对疾病带来一些力量;当你痛的时候,这个宗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有一次许乃深第一次出诊一个患者家庭,注意到这家屋檐下有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燕子窝,许乃深和他们聊起来,在潮汕民俗里,家里有燕子窝是件好事,他知道这一定是这个家庭在乎的事情。
他会根据家庭成员之间说话的样子,家属对患者病情的了解程度,甚至当医生进卧室为病人进行检查时,家人是否跟进去,用来判断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一个患者问起许乃深自己还有多长时间,许乃深从不会直接回答,就会问他为什么会这么问,心里是否在害怕什么。很多时候,许乃深也需要重复灌输给患者一个信念:「你不是家人的负担。」
社工的工作是要满足患者和家属在灵性方面的需求,用许乃深的专业术语来说,他们的工作要满足患者和家庭「身、心、社、灵」的需求,灵性需求,亦即精神需求,要摆在曹伟华满足的身体需求之后,曹伟华首先得保证患者免于疾病带来的疼痛和不舒适,在这之后,许乃深的工作才能更好地进行。
疼痛治疗是姑息治疗里最首要的环节,癌症的疼痛发病率高达84%,有很多病人都提到过,相比起死亡,自己更害怕疼痛带来的折磨。每一周,曹伟华都要向不同的病人以及家属了解病人的身体情况,了解他们的疼痛状况。
曹伟华觉得,同理心很重要,但没有亲身体验,人其实是很难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他对患者和家属的选择大多数时候都尊重,并不带有一个权威医生的傲慢。有人要吃中草药,有人要用靶向药,曹伟华会谨慎告诉他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并不打破他的希望。她知道,希望是患者和家属之间的纽带,是他们对彼此存在的珍视与肯定。
四
既然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无法避免,那姑息治疗对每一个饱受死亡前痛苦折磨的人来说都有其必要性。
但根据WHPCA(全球临终姑息治疗联盟)估计,在全球有需求的人中,只有10%的人真正得到相应的姑息治疗。许多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因为目前无法提供基础的疼痛管理,数百万人不得不在痛苦中死去。
全球都在面临老龄化,中国的情况更为严峻。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估算,到年,中国将有13%以上的人口达到65岁以上,相比之下,全球人口的这一比重只有11%(在印度只有6%),这意味着中国的一般医疗体系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对姑息治疗也会有更迫切的需求。
《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年度死亡质量指数——全球姑息治疗排名》,在参与评估的8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71位。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姑息治疗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然而中国仍然排在乌干达、俄罗斯、蒙古、加纳、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家之后。
报告显示:「中国的姑息治疗整体供应有限,而且质量不高。仅有不到1%的人可以享受到姑息治疗服务,并且大多数临终关怀机构都集中在上海、北京和成都等大城市;没有国家战略或指导方针;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和供应有限;医患沟通不佳。」
中国政府曾经出台过关于姑息治疗的战略,但这只是一份宽泛意义上的声明,不包含清晰或具体的里程碑目标,也没有准备好实现该战略的清晰机制。很多需要面对大量临终患者的肿瘤科医生都表示,自己从未学习过如何与这些病人谈话。
姑息治疗在中国推广起来困难的另一个很大原因还在于这项医疗成本并未被医保所覆盖,即便在中医院——医院——病人也很难承担每个月几千元的看护费用。
姑息治疗的缺失,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我们或我们的家人必然要在死亡面前饱受折磨。
年,青年教师秦岭给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写了封信,讲述罹患晚期肺癌的父医院,历经强制出院、入院无门,只有走后门、说谎、送礼都无法获得一张病床的绝望。
没有人统计过需要临终关怀服务的人数,但在中国每年万的死亡人口里,有万人死于癌症——晚期癌症疼痛的发生率高达80%。还有八十岁以上、身体极度衰弱,患有多种疾病,脑萎缩、老年痴呆,甚至没有记忆和理性的老人。
秦岭面临的困境几乎指向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积极治疗是疾病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当疾病一旦失去了治疗的机会,无论是病人,还是亲人,都失去了在这个世界的坐标。
在中国,治愈性治疗方法一直占据着医疗战略的主要地位。当我们被这个以治愈为目的的医疗体系抛弃时,还可以去哪里呢,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更好的告别方式吗?如果没有足够的姑息治疗服务,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晚期癌症病人和家庭都将被这个世界驱逐,在痛苦中死去。
五
许乃深告诉我,观察一个家庭就像剥一颗包菜一样,你要一点一点才知道,这个家庭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在一个患者家里,许乃深注意到癌症晚期的父亲搬出卧室,在楼梯口支起一张临时床铺,横放在在一楼和二楼中间,每天都睡在这里,家人不理解为什么。
许乃深和他聊才发现,曾经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在生病之后,原来是很寂寞哀伤的。躺在卧室床上被家人照顾,也可能意味着被抛弃,所以他选择在楼梯口,继续观察着这个家庭的情况,发生的每件事,任何时候,他都不至于被遗忘。许乃深把孩子都叫到身边,告诉他们爸爸虽然生病了,但爸爸的角色还是一样,家里有时还是要多和爸爸商量,听取他的意见,不要让他有被落下的感觉。
当然,许乃深也碰见过戴口罩回来看望患病母亲的女儿,一次之后就落荒而逃,女儿总害怕癌症会传染,也不知道母亲在这个时候有多需要她。
大多数人思考起自己的死亡时都会感到恐惧,如果可以,医院和养老院吧,那样人们就不用去谈论也不用去熟悉它了。但是与垂危的病人开诚布公的交谈应该成为姑息治疗相当重要且平常的一部分,应该变得像医生和感冒病人讨论感冒药一样。
在死亡面前,能让人闪闪发光的通常不是求生本能,而是一个人的灵性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这种时刻许乃深见过很多。
今年6月,当刘树清的女儿来到宁养院时,她的内向和冷漠让许乃深印象深刻。她只传达出了家里有一个暴躁的癌症晚期的父亲,至于具体的病情和需求,她并不太清晰。
刘树清的家在汕头市区的一个廉租房里。他蜷缩在自己破旧的木床上,眉头紧锁,神情痛苦,不时因疼痛发出呻吟。今年6月,刘树清的大女儿刚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也是这个月,刘树清被诊断出右肺癌并多发转移。刘树清是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木工,十年前,他的妻子因胰腺癌去世,和大多数必须承受灾难的父亲一样,刘树清打很多份工,抚养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即便五年前他因青光眼致盲,他的努力也没有减少半分。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父亲,肩负起保护女儿的责任。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他和女儿在沟通和情感上的疏离。患病之后,因为疼痛、害怕、绝望而抑制不住的暴躁,更让两个女儿不知所措。
每个夜晚痛的时候,刘树清就用凸出来的床板边沿顶住自己的背脊,咬牙捱到天亮。
当许乃深和同事第一次去到刘树清家里时,刘树清就在他们面前痛哭起来。和一个陌生人诉说自己痛苦的一生是一件更容易的事,许乃深为他递上纸巾,肯定了他遭受的痛苦,也肯定了他的坚强。
医生为刘树清开了止痛药让他在日常里的疼痛得以缓解。
虽然看不见,许乃深却感受到刘树清有很强烈的灵性需求,家里放着很多他在失明前读的书。第二次到刘树清家里时,许乃深带了一本书,邀请刘树清的女儿为父亲朗读了其中卡尔基写的一段话,他觉得那是刘树清的心境:「我相信,我们内心的平静和我们在生活中所获得的快乐,并不在于我们身处何方,也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更不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而只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而只在于我们的心灵所达到的境界」。
这是父亲与女儿之间难得的一次在传递心电流的交流,「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可以给你带来平静」。
8月,刘树清的病情急转直下,基本吃不下东西。8月2日是刘树清的生日,在征得同意之后,许乃深带着同事来为刘树清过了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生日。他带着一个写着」点亮心灯,回眸人生「的蛋糕来到刘树清床边,他本以为刘树清必须躺着过完这次生日,没想到刘树清要求在女儿的搀扶下坐起来,这是让许乃深感受到灵性拥有无穷力量的一个时刻。
大家围坐在蛋糕四周,为刘树清唱完生日歌。内向的女儿第一次哭着向父亲表达了对父亲的感谢与爱意,感谢他的坚强与付出,刘树清也流着泪向女儿表达自己的歉意,希望女儿原谅自己在患病之后的不由自主和无能无力。
第二天,许乃深开始为刘树清联系相关的后事准备。8月7日,刘树清去世。8月9日,刘树清的两个女儿来到宁养院,交给许乃深一封信,上面写着:「父亲离开的那刻脸上仍带着微笑,我们知道忍受病痛折磨的他感受到了幸福。」
许乃深第一次去刘树清家时,注意到他家窗外的苦楝树,这是在潮汕地区常见的一种树,开紫色的花,那时候,苦楝花总飘落在刘树清的窗台上,他不曾注意到。苦楝树是菩提树的一种,指引人们开悟,许乃深觉得这种树像极了刘树清苦涩又完美的生命结局,「只要人真的想通了,他就能懂得放下」。
很多时候许乃深都觉得这份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情,能从事这份工作,是他的福分。
人在临终前的愿望都不尽相同,有人愿望很大,有人愿望很小。
有基督教徒的愿望是能吃一顿圣餐,许乃深请来一位院牧,在患者家里为她做了一顿圣餐,唱了圣歌。那天,这位癌症晚期患者为自己穿上了一件红衣服,容光焕发,那一刻许乃深几乎感受不到她是一个濒死的人。
踩三轮车的黄先生,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帮助5个人重见光明。
也有关系破裂的夫妻,在宁养院介入之后,才终于明白了各自的心意。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和一辈子作为家庭主妇找不到自我价值的妻子,各自都换上了最好看的衣服,牵着手,让许乃深为他们拍下一张照片。这不是一段自由恋爱,这是他们第一次牵手。
有一次许乃深为患者和家属准备了一张贺卡,左右两边分别画上一个心,心里写上他们各自的愿望,把贺卡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愿望就「心心相印」了。有一位患者写的是:「我希望我走的时候,我的爱人不要太伤心」。
有人喜欢所有亲人都聚在一起,等待那个时刻。也有人希望自己能独自度过那个时刻。有一个患者,他一定要等到帮助过他的宁养院工作人员到来,道完谢,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
有一些患者,已经在弥留之际了,家人却还未察觉,这时候宁养院的工作人员会让周围的人保持安静,人的听觉会最后消失,他们可以走到患者耳边说一些让他安心的话。在最终的那个时刻,人们需要道歉、道谢、道爱、道别。
宁养院就在汕医院的后院,不是一个很显眼的位置。大堂摆着一张柔软宽敞的皮质沙发,浅色地板,灯光总是被工作人员调到最舒服的亮度,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同样摆着一张宽敞舒服的布艺沙发,天花板上挂着一个被绿色植物装饰的鸟笼,这个房间偶尔用来进行一些私密谈话。虽然很容易遇见坐在沙发上流泪的人,但每周来取药或咨询的患者和家属都能在这两张沙发上得到暂时的安慰或释放。
曹伟华和她的同事就在一门之隔的办公室里办公,办公室再往里的房间,存放着已经结束服务的多人的资料,它们被放置在一个需要靠轨道才能推动的巨大铁质柜子里,李文苑为我旋转开关,个家庭在生命末尾的故事和愿望就在我面前流动起来。
办公室的门几乎总是打开的,那是一个永远不会拒绝人的推拉门,每一天曹伟华和她的同事推开这扇门,就能看到大堂沙发上方挂着的那幅毛笔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