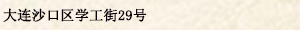ldquo怪玩家rdquo们的再
啤酒小妹站在风里,西安5~12度的天气。
她背后是粉刷一新的公厕,大概是前段时间文明城市评比才弄好的。公厕的月白,和啤酒小妹的高筒靴同一颜色,门口还摆上了若干盆假花,喷了大概有半斤的空气清洗剂。一阵风吹来,公厕的腥臭、空气清洗剂的甜腻、啤酒小妹香水的若即若离,充分的混合在一起。有些怪异是不容置疑的,但你得承认,怪异得很有风情。
我为啤酒小妹感到无奈,她大概认为这条巷子通往背后的若干小区,而且现在快到下班时分,所以大概率会有人买她的啤酒。她忘了基于同样的理由,这里是商家必争之地。该地点早被15块钱的炸鸡、8元的炸油馍,还有买一斤送半斤的核桃酥充分占据。啤酒小妹被挤到了公厕门口,她的脸冻得泛出小块儿红斑,和裸露的一截大腿同一色调,她尴尬、无奈,又不得不继续下去。
我也比她强不了多少,这都拜大宇所赐,是这个货把我约到这里,而他自己却迟迟不出现,于是我和啤酒小妹陷入同样的处境——被等待反复研磨。
“来两箱!再送我个起子吧!“大宇的声音在我背后炸响。啤酒小妹对从天而降的生意有些手足无措,蹲下搬啤酒时,差点撞翻了形单影只的广告支架。
两分钟后,我和大宇一人一个箱子呼哧呼哧的上楼,这是一所学校的教工小区,要扫码、刷卡进入,但却固执的没有安装电梯。啤酒箱子重得像钢琴,大宇家却在六楼。
“你,你觉不觉得,那个卖啤酒的女娃,长的像艾琳?“大宇突然说到。
“艾琳嘛,《寂静岭4》里的那个?”大宇重复了一遍。
艾琳·加尔文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你个瓜怂”,因为气力正被一缕缕地抽干,实在组织不起嘴唇的合理运动。
娘炮
大宇找到我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怎么愿意和他见面的。
我那时有我自己的烦心事——写了若干篇不知所云的玩家故事,发了若干篇水平不咋地的游戏评论,但也就是停留在若干而已,脑海中的文字像定格在墙上的蚊子尸体,越来越刺眼的的同时,却无法向任何地方飞去。
这种情况就像西安的冬天,看似来势凶猛,说出来也就不过如此,加上西安的冬天越来越爱下雨,雨大的让人不知所措,飘洒着一切无聊、无奈、以及自惭形秽,害苦了等待晴天的人。
就在等待晴天的某个晚上,我发了一条信息在群里,开始是一个马保国五连鞭的表情图,还附上了一句话:“太无聊咧么!有人请喝酒么?”
10秒后老易回复:“无聊刷煤去!”然后无人发言,一切沉默。直到我玩了两个小时的《真人快打X》,大宇突然回复了信息:“周末,来我家霍酒,咋样?”
这条信息是私信,没发在群里,大宇和群里的人都不太熟,但我还是立刻回了:没问题,然后附了一个“棒棒哒”的表情。
后来我的游戏兴致全无,纤细而微小的想法开始爬出皮肤:我和大宇不熟啊,他干嘛要请我喝酒?还有,为什么我没回复“么马达”而要认真回复“没问题”,还附上了一个很娘炮的表情?
说到娘炮这个话题,大宇上学那会儿总是带着深蓝色的套袖,时间长了会露出带点点白花的里子,被他小心的掖藏在手腕里。除了娘炮的套袖之外,大宇的书包也很出名,帆布的质地、晴天的颜色,上面印着一行黑色的行楷字体:XX工业研究所,有意无意中标榜着“这是研究所发的,我是研究所的子女。”
于是,每当看见大宇走进校门的时候,我们都对他产生了某种幻觉,感觉大宇不是正在走进高中学校,而是昂首阔步地走进研究所,而且下一秒,他就会从书包里掏出个古怪装置往地下一扔,然后砰的一声变出满是齿轮的先进机器。
玩游戏也是一样,或者说,我们从没见过玩游戏的“前戏”像大宇那么娘炮。他会把手柄用餐巾纸认认真真擦一遍,凳子也要挑选个最干净的,然后书包规规矩矩的放在电视机上,哪怕包机房老板吼他也无济于事。
他的游戏行为同样很怪异,当我们所有人都在玩实况的时候,他却对FIFA情有独钟。被实况包围时的感觉,大概犹如在烤肉摊使用银质刀叉吃西餐,但大宇却不为所动,并为自己每个进球而默默鼓掌——是的你没听错,根本没人和他对战,他自己给自己鼓掌!
在高二某个炎热的午后,FIFA的光盘终于消失了,大概包机房老板对大宇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他不想看着一个怪异的人独自占领PS主机,而且一占就是2~3个小时。
之后大宇迷上了《寂静岭》,在大雾弥漫的环境里独自跑来跑去,这在炎热的夏天更加不合时宜,包机房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的问他:唉,伙儿,这是啥游戏么?你这是弄啥哩?那段时间里,大宇的套袖由蓝变黑,后来噗拉拉掉下结块的污垢,他的眼镜镜片里满是一片雪白的大雾。
“瓜皮么!”我那时抱怨,声音控制在周围的人可以听见,而大宇听不见的程度。然而周围的人却表情麻木的看着电视,见证着大宇被肉乎乎的怪物围攻、锤击、失血、直至死亡,最后报以一声叹息。
“想啥呢?得是想葛玲呢?”
大宇的一席话语,突然把我从高中时期带回到20年后的现在,他打开一瓶啤酒的同时,还开了一个十分暴露年龄的玩笑。
这个玩笑太过古老,来自90年代葛优给双汇火腿肠打的一支广告,古老到早就失去了笑点,只剩下不合时宜的生硬。生硬的和嘴里的啤酒有一拼,比9度醇厚却没有9度煞口,比干啤淡雅却没有干啤凝练,更像是一小截冻僵了的奶酪,正融化在胃里。
大宇的家没怎么变,桌上还是摆满了各类英语教材,因为大宇是中学英语老师,电脑里还是常驻着《FIFA》和《寂静岭》系列,不出我所料。
我喝了一口啤酒,玩起了《寂静岭4》,发现完全不适应游戏的气氛。《FIFA》则依然操作别扭,运球的感觉犹如端着盘子跑步。大宇在旁边认真的喝着啤酒,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终于,我一个大力射门结束了游戏,模糊的足球朝着看台飞去,守门员没有做出任何扑救动作。
大宇家《FIFA》和《寂静岭4》的光盘倒是保存得很好
“可惜了!”大宇仰脖喝酒“轻点D,用三分之二的力量射门,必进。”
“疯了?你咋喝的这么快?”我有些惊诧地望着大宇。
“田菁菁马上就来了!”大宇又开了一瓶,答非所问。
闷骚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一本同学录“我最喜欢的”的一栏里,写下过这样的话语:踢足球、听音乐,看电影。同学录是田菁菁的,五颜六色的纸张,厚厚的组合在一起,带着橘子皮和西瓜霜的清香,仿佛一个刚刚烘培成功的水果蛋糕。
田菁菁留给我整整三页的空间,但我写到第一张时就泄气了,匆匆在“看电影”后面又加上了个“玩游戏”,而且字体很大。
填上“玩游戏”我又开始后悔,劈里啪啦摇晃了半天涂改液瓶子,认认真真涂了三个白色的正方形,于是“玩游戏”裹上了裹尸布,一具欲盖弥彰的木乃伊。我那时告诉自己:你是对的,不应该提玩游戏,没必要再和田菁菁扯上关系。
田菁菁和大宇一样,都是研究所的子女。不过田菁菁不背帆布质地的书包,而是围着紫色的马海毛围巾,到了夏天,就换成圆溜溜的汉奸式墨镜,唯一不变的,是骑当时流行的山地车。
那山地车至少有16速,数个大小不一的齿轮咬合在一起,速度快的时候,是丝丝的轮胎熨过马路声,速度慢了,就变成咔咔咔的齿轮运动声。田菁菁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男孩都会摆出最帅的Pose,那是下意识的动作,随着她骑车离去而转瞬即逝。
记得那时田菁菁是短发,永濑丽子的那种发型,她的个子蛮高,腿尤其长,骑车的时候,脚踝处总会窜出黑色的健美裤角。
永濑丽子
我在大课间时,经常给田菁菁买牛肚夹馍,并非刻意,而是生意。卖牛肚夹馍的是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到了高中就对上学丧失兴趣,变成了校门口夹馍摊的老板兼晚间砂锅摊老板,“自食其力”与“混社会”的Buff越来越强。
自然,我买的夹馍牛肚特别多,辣子特别给力,于是我“理应”帮别的同学代买夹馍,田菁菁也不例外。况且每次买夹馍的时候,田菁菁总是挤不到前面去,她总是很有规矩的排队,即使所谓的队伍只停留在她的幻觉里。
在某个冬天的课间,我递给田菁菁一个薄如蝉翼的包装袋,包装袋里的夹馍鼓鼓囊囊,红色的牛肚呼之欲出。记得过了好一阵儿,田菁菁才把夹馍吃完,她吃任何东西总爱微微冲着墙壁。“谢谢啊。”田菁菁对我说,我有些惊诧,毕竟我代买夹馍是要两毛钱手续费的,何谢之有?
“呃,不至于吧,你咋哭了?”我更惊诧地反问。“没事儿。”田菁菁不好意思地扭头擦了把鼻涕:“刚才忘了告诉你,辣子少放点儿。”
后来田菁菁经常跟着我们打游戏,车也不骑了,而是驮着一个矮胖的小姐妹,他俩跟在后面有说有笑,像是一对刚放学的母女。
田菁菁最开始并不玩游戏,包机房的环境和味道大概一次次的打击她的勇气,老板总是没日没夜的炖着貌似永远也吃不尽的羊肉汤,然后兹的一声浇到黑瓷大碗里,吸溜着皮带宽的面条。有几次老板还冲着田菁菁喊:“来耍么妹子,耍不好不要钱!”
田菁菁只是尴尬的红着个脸,装着与小姐妹聊天。隔着包机房的棉布门帘,她俩总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完毕之后就是一阵惊悚的笑声,声音大的好像故意让谁听见。
田菁菁玩的第一款游戏是《山脊赛车》,不知谁给她走进包机房的勇气。当时她和大宇对战,明显不是对手,但这并不表明大宇的水平有多高,因为大宇是我的手下败将。
按照第一次游玩的客观条件考量,她的水平还算不错,没有和很多女孩那样手眼不一,一个劲的混淆前进和倒车。不过田菁菁明显不明白《山脊赛车》的系统,更看不清道路的指示牌,而且一旦使用氮气喷射,赛车就直直冲向墙壁。
每撞上一次墙壁,包机房里的众人就“丝丝”的抽凉气,撞得多了大家开始“唉唉”的叹息。这使得田菁菁更加紧张,开始犯手眼不一的毛病,每每撞车一次就焦急地看我一眼,然后捂着嘴笑笑,慌乱地摇晃着手柄。好像那手柄已经具备体感功能一样,好像我会挺身而出帮她夺得胜利一样。
山脊赛车4
我当然不会!我头脑清醒,绝不会错意。
毕竟我是那时公认的《山脊赛车》高手,我对所有车辆的性能谙熟于心:
DRIFT型速度不行,但操控性一流;GRIP型爆发性强劲,但稳定性要差点意思。最为关键的是,他俩都是真正的赛车,高速的赛道是他们的舞台,而我那时的梦想是拥有一辆山地自行车,16速的就行。
我买山地车的钱是借老易的,断断续续过了两年才还清,记得还是在土门或者西稍门买的“贼车”,为了避免被失主认出,还贴了许多Fido的贴纸,一旦骑得快一点儿,贴纸就在风里哗啦啦作响,像是某种昆虫正在兴奋的叫喊,又像是它在振翅挣扎,然后一寸寸的死去。所以,这决定了我那时根本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尤其是对田菁菁,我的角色更适合给她买买牛肚夹馍,仅此而已。
再说大宇当时在追田菁菁,情人节的时候还买了五条金帝巧克力,田菁菁果断的拒绝了他,那巧克力是榛子口味的,含在嘴里,舌头立刻会陷入甜蜜的泥浆。我和老易还安慰并鼓励过大宇,绝非假惺惺,我甚至已经帮大宇和田菁菁设想好了他们的最终结局:
大学恋爱,毕业结婚,然后在研究所里作为小有名气的学者而广受赞誉,会很早就拥有三室一厅的房子,会养一条到处尿尿的泰迪,偶尔还会在朋友圈里发出国旅行的照片,回来之后和我们经常聚会,分享我们很难企及、所以实际没什么用处的旅途趣闻以及心路历程。
而我们会假模假样的啧啧称奇,接着把尴尬的心情伴着红酒送进胃里,化成血液之后会酸眉醋眼的在心里吐槽,但在朋友圈里还要每时每刻相互点赞,为了所谓的友谊。
阴险
“好狗日滴,都开吃咧?“进门的不是田菁菁,而是老易。他打乱了我对往事的胡思乱想,但没留心我眼里的惊诧——怎么?大宇也偷偷叫了你?怎么?你也答应了?
老易没换鞋直接跑进厨房,抽着鼻子笑道:“我还以为你几个都吃上咧,原来才刚炒菜!”老易是对大宇说的,他带着个围裙,正在扒拉锅里的蘑菇,样子显得很娘炮,炸蘑菇的动作却不专业。他把老易推进屋里并叮嘱他把鞋换了,但老易却光着脚坐在凳子上,拿起手柄对我吼:“来,弄!”
15分钟之后,比分是7:2,我2老易7,我选的意大利对阵老易的英格兰。“日!你不是不玩FIFA嘛,可又忽悠人!”我把好奇暂时压在心里,扔下手柄埋怨。
“是啊,我是不太玩FIFA啊,否则你还能进俩球?“老易掏出根烟点上,又跳下椅子找来烟灰缸。我十分不甘心,提出再来一盘,这回比分明显好看多了,4:0。
“不会吧,初恋情人儿要来,把你弄湿塔咧?!”老易幸灾乐祸地抽着烟,不停的把烟圈儿吐向屏幕。大宇连忙给烟灰缸里倒了点啤酒,然后把瓶子塞给了老易。
“用欧文当前腰,会比较厉害,迅速插上得球就射门,进球跟作弊一样。“大宇对我说到。老易听完笑了,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熄灭:“大宇你可不敢胡说啊,你还是人民教师捏,整天作弊作弊的胡咧咧,小心别人举报你!”
大宇选择当教师完全出于自愿,但对于学校来说,就是一种受迫性判断失误。当时学校已经连续两年没出过清华北大的应届生,而大宇二模考试的成绩,超出两所学校的提档线十几分。他无疑是荒年里确凿无疑的丰收果实,怎么可以,又怎么弄够去上师范大学呢?
学校把责任踢给年级组,年级组又把责任踢给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没把责任踢给大宇,而是压到我们身上——你们怎么可以,又怎么能够勾引大宇玩去游戏呢?
大宇数次表示玩游戏完全出于自愿,如同他报考师范学校和喜欢田菁菁一样,但老师根本不相信他会与玩游戏和早恋搭上关系,除了我们这些人的勾引,没有其他原因。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人不满意又找不到真正原因之时,总喜欢对最软弱的部分下狠手,于是大宇再没机会走进包机房,他爸他妈是他身边的哼哈二将,形影不离。
不过这一切丝毫无法改变大宇的志愿,他还是以超出北大19分的成绩上了师范大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有些险恶的暗自窃喜:超出19分又能怎样?上的学校还不是和我一个档次?田菁菁则去了南方一座小城,纺织学院,二本。据说那里经常下雨,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卖牛肚夹馍的小摊。
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信誓旦旦的彼此确定:上了大学也要常见面,至少一年一次。结果直到大三第二学期,聚会才稀稀拉拉的来了不到10个人。
聚会是大宇撮合的,定在解放路的“千家粗粮王“,大家明显兴致不高,38元一个人的自助餐费,大部分人扭扭捏捏的不想交。不知是不是为了让38元更划算,大家开始猛灌啤酒,香辣虾的红壳成片的堆在每个人面前,都没有头颅和长腿。
不知是谁提意,要去当年学校的包机房,于是一伙人晃晃悠悠的去打车,但最后都是大宇结的车费。
包机房老板没变,还是那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头,只是他和包机房都明显的在缩水,甚至感觉任何东西都在变小。一时间包机房里烟雾弥漫,《实况足球》《山脊赛车》《FIFA》的音效震耳欲聋,话题从自己上的学校多么多么牛逼,慢慢变成预测世界经济的形势,然后又从自己曾见过多少多少名人,慢慢变成谈论当时班里的女生。
自然,田菁菁成了主题,她的胸、她的腿、她永濑丽子的发型,她的山地车都成了那天包机房的热点话题,有人说田菁菁在南方发了,据说和个富二代结婚了,学都不上了;立刻有人插嘴,啥结婚啊,就是被包养给人当二奶呗,哈哈哈。
在对田菁菁的各种虚拟揣测之中,人人好像都高尚和伟大了起来,又仿佛人人都找到了自己最坚硬的部分,而且彼此都十分确信。倒是大宇一言不发,他车轮战般的击败了数个对手,2:0、3:0、5:1,他不断刷新着自己的最快圈速:2分07、1分59,1分53。一个同学大咧咧的给大宇递烟,还把烟硬塞在大宇的嘴里,他刚刚放弃了比赛,因为大宇马上就要刷过他一圈:
“大宇啊,你《山脊赛车》耍镇好,得是因为田菁菁这娃长的像永濑丽子?”
“这人不是永濑丽子,这是深水蓝。“大宇把烟从嘴里摘下,慢慢的还在那个同学的手里。
“傻逼了吧,人都认不全,你还玩锤子啊你!”老易在一旁总结。“怎么能说傻逼呢,应该是特别傻逼!”我对老易认真的说,大宇终于忍不住,笑了。
大宇的《山脊赛车5》光盘,封面上的模特是深水蓝不合群田菁菁姗姗来迟,因为停车的原因,她在大宇楼下把车子横过来又竖过去,就是停不到面包车和一辆SUV之间。
电话是打给大宇的,但大宇让我去帮田菁菁,因为他正和老易鏖战FIFA正酣,为了一个边线球不断相互揶揄。田菁菁毫无意外的老去,或者说更成熟了,她像家庭主妇一样,慢吞吞地搬下超市装的蔬菜,然后从后备箱里,拎出一打百威啤酒。
我有些尴尬,就拿田菁菁的身高开玩笑,我说好久不见啊田菁菁,你怎么越来越高哈。田菁菁眨了一下眼睛回答,我穿了高跟鞋啊,你没发现?说完就一手扶着车门,一边认真的抬起脚,给我展示足有6厘米的黑色细跟。
上次见田菁菁还是两年前,她因为自己的业务找到我,通过大宇和老易。
当时她自己刚开了印刷厂,苦于没有业务,说是印刷厂,其实就是3~4台印刷机器,5~6个员工。我当时在厂里的机动处,按说八竿子也帮不了田菁菁的忙,但最终还是通过层层的关系,给她联系了一项印制宣传册的业务。
数量不多,只有出头的册子,而且由于是国企的关系,田菁菁大概赚不了太多的钱。半个月后,田菁菁顺利交货,我曾经想好了拒绝她的理由,因为按照一般程序,她会请我和厂里的业务代表吃饭。奇怪的是,田菁菁请客从来没叫过我去,只是在领汇票的时候托人带给我一个全新的PSP。
“千万别见外,and生日快乐”包装盒上一行清秀的小字,外加一个吐舌头的笑脸,田菁菁的习惯,田菁菁的字体。那个PSP我只是偶尔玩玩,因为我当时只对NDS感兴趣,某个晚上我昏昏睡去,醒来时屏幕突然花屏,而且充电器莫名其妙的丢失,我懒得修理,更懒得寻找,就此放弃。
我后来再没见过田菁菁,但知道她确切的消息:印刷厂关张了,又搞起了设计室,设计室后来也倒闭了,又开起了服装店兼服装定制,谈过一个男朋友,后来分手了,至今没有结婚。
这些消息都是大宇告诉我的,而且非常主动,仿佛他是我和田菁菁之间的通讯员,即使我认为他不知道我和田菁菁之间微妙、幼稚、无聊,未曾发生,也不能怎么样的曾经。我偶尔找过大宇,因为他那时已是某所重点中学的英语老师,周围的朋友托我让大宇找找关系,无非是因为家里都有个“英语成绩让人崩溃”的孩子。
我惊奇大宇一直保持着玩游戏的习惯,喜欢《寂静岭》,买了很多正版的游戏碟片。某个下午,我和大宇一起玩游戏,彼此几乎没有交流,我看着大宇操作玛丽亚在大雾中行走,抚摸詹姆斯的脸,然后隔着冰冷的监狱栅栏,冲着屏幕慢慢的说:“I’mnotyourMary。”
“你知道吧,田菁菁其实……”大宇盯着屏幕说了一句。我说我知道知道,然后岔开了话题。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正被大宇的寂静岭之旅吸引,他在寂静岭里闲庭信步,机敏的好像在自家院子里穿行。
直到此时此刻,田菁菁站在我面前,我也觉得我当时是对的,总的说来田菁菁是个局外人,大宇,老易,我们所有人在某些方面,都是彼此的局外人。大宇的焦盐蘑菇毫无意外的失败了,而老易的红烧带鱼也发挥失常,田菁菁的手撕包菜几乎没有炒熟,我做的青椒炒肉则只能吃出姜丝的辛辣。
但这豪不影响我们喝完了两箱啤酒外加一打百威,当我自告奋勇的下楼买酒的时候,啤酒小妹正在收摊:“不好意思,只剩四瓶了,要不您等我一下,我打电话调货。”我说没事没事,四瓶足够了,我们正好一人一瓶嘛。
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这次聚会的理由,聚会的目的,聚会的人员组成,大宇貌似一直都瞒着我。不对不对,不只是大宇,共犯还有老易和田菁菁。我自认为和大宇不熟,但别人却真把我当朋友。而这场聚会也根本没什么心机,或许只是几个爱玩游戏的怪异友人,阔别多日想再见一见罢了。
这种感觉如此熟悉,因为不止一次发生过了。而且总是我想不通,就像寂静岭里的小女孩劳拉,坐在墙头上指责詹姆斯:“Huh?Areyoublindorsometh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