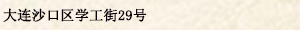岁月的匹夫
她应该被比作夏天的橘子汽水,或者是司汤达的盐树枝。
命运的battle
很久以后,裴然总是会想起最后一次见陈欢屿的那个晚上。
夏天总是太长,在看不见尽头的夜晚喝了无数次啤酒,却还没过完。在裴然的记忆中,那晚陈欢屿出现得有些莫名其妙,他和工作室的同事一起吃完夜宵回去,看到她正坐在路边杂草丛生的石板上。
她低着头,于是裴然先看到她的头顶。那时候她留短发,发量很多,又是天生的自来卷,一头乱发在夜色下也显得蓬蓬勃勃。
只有裴然注意到了她,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顶。陈欢屿仿佛知道是他,并没有立刻抬头,只是轻轻晃了晃脑袋,她的发在裴然的手心摩挲了好一会儿。
同事调侃了几句便返回工作室,裴然蹲下来问陈欢屿:“这么晚了,你肚子饿不饿?”
她好似松了一口气,神经松弛下来,很认真地点头。
裴然开着工作室的吉普车带陈欢屿去吃大排档,夜宵摊离得远,路上有一截没有路灯的窄路。
石子路很颠簸,陈欢屿却乐在其中。她歪着头注视着窗外被车灯映照一闪而过的榆树:“你说师母是不是每天早上都从这条路开过,然后去工作室工作?”
“应该是的。”
陈欢屿用有些怜惜的口吻说道:“很辛苦啊,要开那么久过去。”
她口中的师母是蒋筠,当下业内最炙手可热的雕塑家之一,作品风格鲜明,以展现女性风貌见长。
除去每周在美院的两次固定授课之外,蒋筠几乎每天都会开五十分钟的车来郊区的工作室与大家一起工作。她开一辆很大的奔驰,陈欢屿第一次见她那次,她穿了一条绛紫色的裙子,上衣是黑色的线衫,很瘦,身形很小,因此显得旁边的那辆奔驰巨大。
她没有任何架子,因此陈欢屿很喜欢她,她曾悄悄对裴然说:“蒋筠老师是我见过的最有型的人。”
后来她便经常来工作室玩,她有一些美术功底,因此偶尔也会帮着搭把手。她渐渐和所有人都混熟了,跟着其他人一起喊蒋筠“师母”。
裴然觉得,其实那晚和很多个夜晚差不多,并没有显现出什么不同。他带陈欢屿去常去的大排档吃东西,他已经吃过了,并不饿,陈欢屿径自点了辣炒花蛤和椒盐皮皮虾,埋头苦吃,吐出一堆壳在面前堆积成小山。
他还记得隔壁桌有三个男生正在庆生,买了一个很大的奶油蛋糕,还点了生日蜡烛,就着啤酒举起手机对着蛋糕猛拍。陈欢屿饶有兴味地看了好久,眯着眼睛笑:“很浪漫啊他们,你看,头顶着星空吹蜡烛,很开心吧!”
过了很久,裴然终于意识到,那晚其实很像是一场他们与命运展开的battle。
很多恋人分手的时候,吃最后一顿饭,话最后一次别,他们并不知道,那已经是最后一次。
静寂的冬日
裴然与陈欢屿相识在一个冬日,难得的晴天。他在黄浦江边的私人美术馆负责布展,那是蒋筠的个展,上一站是在台北。
展出的作品很多,因此附带的各种事项也很庞杂,蒋筠和丈夫傅亦聪只在布展初期过来接洽,后面的流程便交给主办方和几个工作室的同事安排。临走前傅亦聪对裴然说:“我们手里还有作品等着完成,所以展览这一块就拜托你了。”
那时蒋筠的作品已经能够轻轻松松卖出七位数,因此裴然深感肩上的担子重。
上海的冬天有霾,江边阴风怒号,将灰蒙蒙的天空吹得越发阴冷可怖,裴然他们在美术馆附近租了一处公寓,房租贵得骇人,他每天需步行二十分钟去工作。
他总是起得很早,在小区楼下的早点铺吃早餐,包子豆浆的热气袅袅升腾的时候,那种身处异乡的漂泊感似乎也会淡薄一些。
布展快结束的时候,事先策划好的大幅导语牌也到了,裴然和广告公司的人一起将导语牌搬到大厅,一回头就看到一个女孩正很认真地在阅读那些文字。
“很抱歉,”裴然走了过去,挡在她面前,“展览还没有开始,我们暂时不接受参观哦。”
女孩露出一个了然的表情,立刻回转过去:“不好意思,我只是路过,看到外面有新展的预告……”说完她反手把大衣里的卫衣帽子套到头上,“这样行吗,我等会儿来看。”
她没有回头,很快就离开了。裴然看着她将随身带着的滑板往地上一甩,女孩轻盈地一跃而上,只留给他一个黑色的影子。
也是在那一天下午,裴然在美术馆附近的广场上再见到她。
那是一处既有台阶也有斜坡和平地的大理石广场,一大批滑板爱好者集结在那里练习与切磋。午后的阳光在他们的脸上镀了一层金色的光,不远处几株腊梅正散发幽香。人群圈出了一块不小的空间,几个外国人正熟练地驾驭着滑板拾级而上,围观者们不时地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裴然捏了捏眼角,站在最外沿看了一会儿,身边突然挤了个人过来:“嗨!”
是陈欢屿,她仍旧套着帽衫的帽子,笑意盈盈的,耳边有一小撮翘起的头发,正仰着脸看他:“要不要加入我们?”
在那个万物皆静的冬季,陈欢屿的出现无疑给裴然寡淡的生活带来了别样的东西,但裴然自己也无法具体说出那究竟是什么。新鲜?活力?温暖?似乎都不是。
黄浦江的风
黄浦江边的高层公寓,售价十五万一平方米。这是陈欢屿告诉裴然的。她是上海女生,说一口地道的沪语,爱吃软烂的甜食,大学毕业后去做了一年数学老师,觉得太安逸了,于是选择去读研。
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正一起坐在黄浦江边吹风,展览已经开幕,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陈欢屿也去看了,票是裴然给的。
作为回报,她邀请裴然去她家作客:“你来上海那么久,去瞧瞧上海人的饭桌吧!”
她说得突然,裴然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对,心里总觉得有些唐突,于是低头笑了笑,不置可否。
江边的风仍旧凛冽,此时他们视线尽头的天空正飘荡着一只风筝。看不见具体形状,只依稀辨得有一点点墨蓝,一点点柠黄,在苍茫的天色的底子映衬下显得越发动荡与破碎。
隔了一段时间,江面有一艘汽船缓缓驶过,他们一起静静地看船,也看船驶过之后留下的水波。
突然,陈欢屿低低地笑了:“莫名想起我以前教书的时候,天天钻空子从学校溜出来,跑到这边来玩滑板。”
裴然很意外:“居然可以从学校溜出来?”
“是啊,”她说,“教两个高一的文科班,很轻松,只要讲解书上的内容和课后习题就行了。那些奥数和拓展太难,根本没人想学。学校隶属一个教育集团,很大,我们每人的办公点就有三处,根本无法查你是否在岗。”
“所以你就翘班?”
“不只是我,我们那一批人中有好几个都不务正业,我起码还会多走几步从侧门绕出去。另一个家伙天天翻墙头出入,我们跟他说有摄像头,他信以为真,就戴着个头盔翻墙头,然后有一天被校长当成逃学的学生抓到了。”
她一本正经的叙述让裴然忍俊不禁:“不是吧!我觉得这也太扯了。”
“是真的呀,这家伙后来跟我一起考研了,现在在厦大读哲学研究生,前几天传来消息说他打算直博了。”陈欢屿的头发被江风吹得飞散开来,她伸手把乱发撩了撩,“后来我妈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选择的机会变多了,所以个个都那么作。”
“是啊,可以选择为人师表,也可以选择痛快地做自己。”
“也是有代价的啊,”陈欢屿说,“现在想再回去教书肯定没那么容易了。但还好我们都不后悔。”
傍晚的夕照
后来裴然还是在年前去了陈家作客,陈欢屿很高兴,再三叮嘱他不要讲客气、不要带东西,他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给她订一盒蛋糕。
途中经过十五万一平方米的公寓,隔着一条路对面是一块已经拆迁的空地。说是空地,其实那里还矗立着一间屋子,孤零零的,远远看去也能发现它的破败与凋敝,该是俗话中的“钉子户”。
大概已经断水断电了吧,那栋房子。裴然想着,又看了一眼眼前那高耸的公寓楼,想起之前一个出国的师兄回来小聚时曾经说起一些话。当时他们喝了些酒,师兄有些微醺:“去年我运气不错,卖出了不少作品,现在住在曼哈顿,有自己的工作室,幸福感爆棚。但一回来就泄气了,过去我们都以为纽约是世界的中心,其实并没有,上海才是……”
透着醉意,裴然依旧记得师兄那时的眼神。他看得很清楚,那眼神里并没有幸福感。
裴然从来都不是很乐观的人,他不经常笑,眉宇间总攒着愁绪似的,给人看起来好像活得很不如意。他的老师傅亦聪欣赏他:“裴然对生活有自己的思考,我们做艺术的,不需要活得太开心。”
傍晚的余晖照进公寓楼的玻璃窗,裴然看着那暖橙色的光,在那一瞬间觉得如果能够住在黄浦江边的公寓里看夕阳,应该会很开心吧。
然后他突然想起了陈欢屿,她总是冻得红扑扑的脸,说话时总是容易激动,面前呵出一团团雾气,像是不知名的精灵,准备突然消失。
正想着,陈欢屿的“嗨,我把我家的地址发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