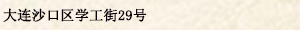农家乐包菜第五道选举
选举是手段,换届是目的。在农村,这两个词被广泛认可为同一件事。
因为农村基层换届选举会产生出来“权力”机构,所以许多乡村文学会带着王朝史书般的色彩来描述其中的斗争故事,增加矛盾情节、彰显人物冲突、制造紧张气氛。我作为一名“过气”的读者,在参与其中之后,才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而且有时候,还很高。
农村换届一般会被要求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十分关心老百姓身边故事的老百姓自己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么重要的新闻点。那段时间,我们总是摁着幸灾乐祸的感情,满怀期待地打听对方村子的故事。
从整体上来讲,农村的换届选举按照《党章》、《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逐步正轨完善,农民对于选举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原本混乱的选举已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形成规矩,偶尔出现的矛盾只能增加周折,多花心血,并不能改变“法制”进程形成的制度趋势。
一、选举这个事
三年一次的农村换届包括支部换届和村委换届,选举是换届中最重要的内容(形式),在近些年成为舆论的焦点后就开始逐步自我成长。
1、过去不是事。
许多农村是由家族逐步发展而形成。家族有自己固有的一套文化管理模式,比如“族长负责制”。在这个基础上的农村管理也就顺理成章的演变成几个家族之间的相互“管理”。所以,过去的农村换届没有什么手续,也没那么多文章。通常由村委组织村里少数“有头面”的人,坐下来推荐商议后确定出村主任及班子成员。因为村委本就是自己家族的“说话人”,这样的双重身份确保“简单粗暴”的换届方式也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就算有点矛盾,也可以通过农村宗族文化给予调整。
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村委会因为家族族长的稳定而稳定,所以,他们会一届一届的连续下去,村长就常常变成老村长,有点“终身制”的味道。另一个方面,普通村民在这样文化熏陶下成长也不会对村长这个位置产生觊觎,不去竞争,就减少了冲突。这种模式看起来很省事,一个村子的命运放在几个人的身上,对他们的“管理”也只靠上级的监督和道德舆论的制约。的确,这个模式也运行了很长时间。
如果农村一直都是这样节奏,经济文化没有什么变化,外部环境也没有什么变化,那文化框架下的管理秩序也不会被改变。但是问题来了,经济发展,而且是快速发展,带来文化政治等新的变化。
2、现在是大事。
接着上段说下去,农村在经济大发展后便开始倒逼原来的管理模式“制度”。首先,农村出现新的阶层,比如“见过世面”的外出务工者、财富爆发户等,就算他们不要求参与村务管理,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被管理者”也会给那些老村长们造成新的问题压力。其次,这些老族长(村长)开始发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跟不上社会发展,经验和威望解决不了新出现的问题,就会瓦解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比如,网络就让他们束手无策。老文化不再稳定,老村长们没有了文化撑腰自然就驾驭不了原来建立在农村文化上的简单粗暴式换届模式。
那就变吧!但抛弃总比建立容易。这是少数人在推动的模式改变,却要影响到全村大多数人。其中有一大半人或许还没有准备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会“三国演义”。一环紧扣一环,最终这套多米诺骨牌把上级党委政府拉进来。政府希望农村稳定和发展,并为此建立村级组织模式,而现在村级组织换届本身会产生矛盾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深层次的介入其中(算是汽车养护的层面,制度本身也要修理保养),所以名义上村民自治下的换届总是需要政府提前“干预”。
应对换届选举拉进各种阶层(势力)后形成的竞争,政府努力要做的便是公平:加大监管力度,严格选举程序,一切依法办事。
一人一票,给予农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一个“太垃圾”的村主任可能使用手段欺骗一回当选上去,但很难依此连任下去(这是选举的优点,这里就不在重复赞美)。难点在于:最广泛性普选式的民主要发生在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最不懂政治的一批人身上。
我发现一些事,但肯定不止这些事。
◆不同于乡镇等上级政府换届工作采取代表们集中开会模式,村级换届因户籍的稳定性和参与的广泛性只能将选区分散到本村每户村民。近几年人口流动加剧,许多经济落后的山区村常住人口远未及户籍人口的二分之一,且以老年儿童为主。执行换届选举规定中“双过半”(参选选民过半,得票过半)的要求十分困难。候选人为了能赢得选举,有时不得不自己去联系那些外出的人员回家参与选举。许多时候是既要卖出自己的人情面子,还要补贴当事人的车票、误工费费用,有形中就增加了候选人的参选代价。
◆程序的初衷是为了规范,形成秩序,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但是随着竞争的不断深入,竞选者的争斗也增加了对程序监督这一个内容,原来用来防止秩序混乱的程序,也可能变成影响秩序的一个由头。
选举委员会中成员素质差异在执行规定动作中出现的纰漏(如,婚丧嫁娶选民登记出入、选票发放监管缺失)未得到及时纠正,在选举后期直接影响换届工作。有个例子:选举结果公布,个选民的村子A候选人获得了张的选票,B候选人获得了张选票,本来压倒性的结果几乎没有异议,但是B提出了某一户人家3个选民漏掉登记了,也就是说这个村应该有选民个(投票前他没有说),这样被质疑后,选举结果就无效了!只好重新按照流程在进行一遍,所有当事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
3、以后还有事。
当然,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新时代总会出现新问题。好在办法总比问题多,这也是基层乡镇干部的能耐。
◆人口流动的问题,我在人口一道中提到过人口外迁改变选民结构。近几年外出人口加剧,使一些农村常住人口尤其是适龄选民锐减。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可以选择的出路越来越多,优秀的农村人才倾向外出务工创业,不愿意留在农村,不愿意为农村服务。相比较传统的农村社会,当前农村两委的候选人候选范围明显缩小。另一方面,村委会服务的对象是留守农村的村民,他们的素质观念等相对落后,对许多惠农政策只看短期,只谋眼前,片面解读,给村委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这些矛盾使得候选人容易把为村民服务的工作看做是得罪人的事,所以在换届年里,候选人会表现得畏首畏尾,同样,在以后的村务工作中,长远性的村务将逐步减少,短期效果刺激性的工作将逐步增加。
原本我们设计用来监督和制约村委的选举(选票)会变成村委畏惧和“巴结”的不作为。
◆选民意识的问题,意识转变重在变化,没有提高或者落后的界定,但会影响选举。科技(工具,如手机)发展和文化传播,带动村民民主意识的变化。制度的践行给农民这一生存群体带来前所未有的个体尊重(历史上农民总是以群体的角色展现在舞台上)。这使得个别人好像身背千年的压抑得到释放,容易在“极端”中走来走去。村民要求民主的意识不断加强,慢慢学会用手中的权力(选票)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常常造成一次性的兑现。
同时,村民的责任意识持续淡化,“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求肩负责任,但谈及责任的时候又常常会听到“我们只是农民,哪里会知道那么多?”。有些村民会在选举时期被威逼利诱就把票投了出去,过后不久又后悔,后悔几乎没有反省自己当时的行为动机,而是跟着骂“乡村官官相护”、“村干部腐败无能”。
还有,有些村民生产生活在县城(外地),个人利益和村集体利益的相关性逐步弱化,不像传统村民(生老病死)一生都在农村,习惯严格遵循组织期望,履行选举权。这些“半农村人”只选择体验选举过程的“猫与老鼠的快乐”,对选举结果不会太在意。
◆竞选规则的问题。选举过程很严,但换届后监督很弱。按照方案,换届所需的工作经费由上级组织支付,候选人无需经费开支。实际上,候选人为了在换届竞选过程中取得竞争优势,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竞争双方势均力敌,成本更高。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许多人把竞选当做一场赌局,一旦落选,候选人将面临经济和“面子”的双重打击。这让落选者心里很不舒服。
基层换届选举,程序上党支部先行换届,再进行村委换届,所以部分村主任候选人在第一阶段支部换届已当选了村支部支委,承担部分村务工作分工。换句话说,这类候选人,竞选成功是村主任,竞选失败也还是村干部。你的竞选对手最终会变成了你的同事或者领导。为了竞选成功,双方很可能结下了矛盾,如果落选后思想认识未能及时转变,就只能是带着矛盾一起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各自又是自身家族(角落)在村中的利益代表,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这种矛盾“对立”给后续(本届)村集体工作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消极应对工作,逆向宣传村委工作部署,甚至刻意捣乱。
另外,一些当选的人如果发现村干部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好(“爱情没有那么美”,也叫“不过如此”)。失望下的工作便无心从事,甚至放任不管。因为在竞选的时候,程序没有要求其必须向村民演讲表态,说自己当选要做什么。没有承诺就没有责任,自治的选举结果很难随便被撤销。而且,村民也不知道后面如何监督、评价村主任是否合格,事前事中事后都只能以自己的利益是否获得?获得多少?作为依据。
二、换届那些人
事情总得有人干,虽然我们常常各自心怀鬼胎,但好在大家的基本目标还是一致的。
1、候选人很忙。
◆他的动机。参与竞选的候选人不管针对哪个岗位(村主任或者村委),主要的动机有三种:
一是希望获得权益。一些首次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因为没有经历过岗位风雨,纯粹依靠自己揣测和感受推测这个岗位有多大的权益,“走在围墙外面听庙堂的喇叭声”。以为当上村主任后就可以决定村民的具体事务,可以随意吃喝获得金钱报酬,可以在村里的工程项目里获得利益股份,但是这套臆测版本里很少会涉及岗位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上级和群众的管理监督。
二是想要获得名利。一些走上致富道路的村民在获得财富所能带来的物质享受后,需要在名分上得到村民的进一步认可。对于一个普通村民来说,他的“身份”除了农民外,不外乎老板、暴发户、工匠,这些都自认为不是“尊贵”的身份。在离开农村,接触社会后,他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受社会认可的名片,摆脱历史形成的这个略带有歧视文化的身份,而他们面前最好的选择的就是村主任(村长)等,这样可以在社会舞台上扮演一个比较深刻的角色。为了这个角色,许多村主任候选人根本不在乎工资报酬多少钱,甚至准备是往里面贴钱以获得民众的认可。(捐资惠民工程)
三是实现自我抱负。这种动机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唏嘘,那就为了理想,但这是真的,人数可能不多。他们对于自己的村庄的规划建设有清晰的思路,并且为了实现这套思路会到处去求人帮忙。在潜意识里,他已经把这个村当做自己的“财产”,所以这份私心也可以算是公心。同时,他们的理想主义往往找不到相应的同道者,对前面的人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容易认为自己的理想只能搞靠自己来实现,结果会一届又一届的竞选下去。
◆他的无奈。讲动机一般都是自己的主动想法,如果是不情愿的被动行为,便是无奈。有些人内心不愿意去担任村主任,感觉是费事、费精力、得罪人的事。但是,家族的利益要求你去争取,在家族人的眼里,你是这个家族最适合去村委里面,占到一个席位,保障本家族一方的基本利益,至少族人不会被外人欺骗欺负。一旦家族认为你最适合的人选去,如果你不去争取那就是自私,就得罪了家族人。一个村民可能穷,可以狠,甚至可以傻,但是绝不能与自己家族做对,那是立足的底线。另一类被动是做了好几届村委,如果没有继续往前走一步去竞选村主任就容易被村里舆论误会自己无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逻辑害死人啊!而且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村务不断规范,村民会认为许多事情只有村主任才可以做主,这样就会对普通村委看低一眼,进而侧面激励了普通村委向村主任争取。
◆他的团队。既然农村有家族,有利益分割,那你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级换届虽然只涉及几百几千人的竞争,如同西式民主竞选组建竞选团队,村级换届候选人同样也有自己的“团队”。以亲朋好友为班底,家族成员为骨干的“团队”未正式公开但实际上获得选举委员会的默认和广大村民的认可。换届期间,候选人严格遵守各项规定,难有出格行为,只能暗斗。此时,“团队”成员却可以肆无忌惮的运用各种“非法”的竞选手段,就是明争。如,带上烟酒之类的礼物到某个特定选民家里游说拉票、作出种种许诺、个别甚至恐吓威胁。
2、投票人很欢。
许多村民并没有把换届当做一次“政治活动”来对待。他们不会去研究谁适合做村长,谁做村长会为村里做什么,他们只在乎谁做村长会对自己比较有利益,谁在今年竞选中给自己的利益最大?选举,此时被当做一个“狂欢”的盛典。一些高票当选村主任不久又被选民骂得无能透彻,问题不只是候选人的“欺骗”,还有选民“滥用”了自己的权力。
利益可以勾兑。为了调动选民的积极性,组织者通常会为选民准备一些实用的生活用品,让村民来投票就可以领取。这些物品并不值很多钱,但收获不管多少,只要是意外就能让人愉悦,或者是体现了一种“福利”给予个人的尊重。另外的一部分利益来自于上述候选人团队给予的问候,烟酒之类的伴手礼价值明显高过了组织方的纪念品。而且,一些选民还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管你几个候选人,只要你敢送,我就敢收。(不收等于是说拒绝,万一以后他当选了,那多得罪人啊!)
身份实现荣光。一个普通的村民,只有在自己节庆之日,如婚嫁乔迁等庆典,邀请亲朋好友,才会形成一个十分融洽祥和的场面,大家都祝贺你,向你道喜,让你感受到主角的快乐。而选举的期间,只要手中握着选票,每个人走在路上,就像怀揣着几十万的存折一样自信,大家会互相尊重,互相递烟敬礼,互相感受当家作主的快乐。另外有影响力的人,此时便会有亲朋好友聚集在周围,讨论各候选人的实力和“恩惠”,体现精神领袖的快乐。
爱恨配上快意。选举平台给予农村中弱者和强者的一次平等对话。如果竞选者是势均力敌的竞争,每一张选票都至关重要,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决定候选人的最终命运。那些平时有过节的人就可以在此时伺机“报复”,平时有恩惠的也可以“报恩”。对于普通村民来说,爱恨的反馈(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基本的道德守则,甚至也会根据自己的情感程度,去为某人主动宣传“拉票”或“拉反票”。
3、组织者很累。
村级换届的组织者通常是乡镇党委政府。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换届选举产生的结果会直接影响这个村此后的工作是否顺利。
要确保稳定。组织者首先要保障换届选举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确保程序合法。虽然我诟病了程序可能带来的影响,但那是个案,对于大多数村庄,程序是换届的重要保障。其次,是要主导选举顺利完成,不能失误让候选人对某个环节挑出毛病,避免一些不满的落选者闹事引发打架斗殴的激烈场面。许多看似波澜不惊的选举其实组织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要实现意图。从工作出发,上级党委政府一般都会物色过一些理想的人选,这些人在以前从事的村务工作中脱颖而出,被上级认为会干事,能完成乡镇等部门交代的行政事务;能在村子里面“震的住妖,扬的起道”保障一个村的基本秩序;能具备一定的自律思想,会尊重领导,“做事有分寸”。但这些人不一定能顺利赢得选举,因为村民的判断标准(角度)没有这么复杂,会习惯按照亲疏、利益关系等衡量候选人,所以组织者要提现预判选举走势,做好思想工作。
要遏制干预。组织者希望理想的人当选,也希望落选的人能够“心安臣服”。这个理想很难,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可能落选的参选者提前退出,减少他的付出,减少他的损失(止损)和怨气。相对这种理想的干预,还有一种是我们不希望的干预。村庄的非“官方”力量对换届选举造成的影响也很费组织者的精力。他们自己并不参与候选,但是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财力等影响力左右选举,希望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代言人)走上村庄管理岗位,甚至只是把这些岗位当做“帮扶”馈赠给亲朋好友,至于以后能不能管理好村庄,并不重要。反正他们一般住在城里。这事让组织者很头疼,因为敢于出水面干预换届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三、评书还有话
1、选举是治病与生病的共同平台。
换届选举是村民自治权的突出表现,村民在换届期间,得到了竞选者(包括村两委)及其团队给予利益和名义的双重尊重。一些村民内心中对村级组织的不满得到安慰与补偿,甚至可以通过投票过程中的恶意行为(故意不投你)来发泄不满。制度的空间有效释放了“民愤”的压力,治了村民的“心病”。另一方面,换届竞选的特点使候选人之间容易产生新矛盾,并延及他们所代表的家庭家族。“派系”的纠纷也在竞选较量中升级演变,个别极端行为形成新仇旧恨甚至导致兄弟反目,家族互相责难。
2、换届是国法与家法的交融并进。
选举方案严格依据法制定,是换届选举的主体框架,是换届顺利进行的基石。在实施过程中,个别村具体实际不能完全按照程序顺利进行,为了尽量减少竞选中产生矛盾,选举委员会可能建议采用“家法”调节,以“家法”的柔性来弥补“国法”的刚性。比如,候选人出现3名以上时,按照规定由选举委员会组织村民代表投票产生前2名,但代表人数只有人口的2%左右,波动影响很大,容易产生冲突。此时,一些选举委员会请比较有威望的人出面劝退部分候选人,或暗示候选人进行“信仰抓阄”等民间做法。
换届包括支部和村委的换届,党支部换届因党员的觉悟相对较高,上级组织的方针政策能顺利落实。后由当选的支部书记及支委组织成立村委换届选举委员会为村委换届奠定了基础。委员们在本村的威望及其能力水平的表现,体升了党在农村基层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委员们熟悉本村村情选情,及时掌握候选人、选民的动态,方便向上级组织反馈有关情况,顺利推进选举。换届选举是全体党员和全体村民的盛事,换届工作为党员与村民就村里的建设与发展所需的人才与项目进行深入交流提供平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