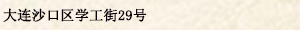农家乐包菜第二道土地
1、因为土地,种出粮食,所以宝贵。
因为土地,换来货币,所以争议。
因为土地,形成农村,所以农民。
2、土地,农村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资源。
土地,理论的集体所有,实际是集体什么都没有。
土地,能种庄稼养人,能盖房住人,能换钱害人。
土地,你归你,我归我,公家归我们。
土地,矛盾的点。
3、耕者有其田,有其田者或不耕
农民、农村、政府都是土地的主人,
谁也做不了谁主。
原来是土地栓着农民,现在是农民栓着土地。
农村的主要资源是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可以是山地、水田、滩涂等,也可以是宅基地。土地是农村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基本底线,有了土地,农村才有意义,农民才有了安心。现在社会发展后,土地的使用价值变的多样性,除了种植农业外,工业、商业都来了。使用价值越多,价值越高,土地成了农民手里握着最重要的一张牌。
一、满村尽带黄金假
故事里的房东、租客、合同一应俱全,相安无事的蜜月期也很长。现在房价上涨了,但房东的收入渠道变了,据说租金对房东来说,不再重要反而手续麻烦,于是就不收了。租客很高兴,群众很满意,那好人房东也很欣慰。但是美好感情没能一直持续,高潮之后留下的落差就像至尊宝说的:“快乐总是短暂的,换来的却是无穷尽的痛苦”。因为发展太快了,事情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我们各自都找到了新的烦恼。于是,无人提及的合同好像保护着各自认为的伤害。
1、承诺有和同,契约没精神。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治上是一种制度,经济上是一份合同,是农户与村集体关于生产用地(农田)产生的租赁合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人是土地生产最主要的因素,劳动者数量及其主观能动性直接影响生产水平,这直接反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套一个理论说:人与土地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促进土地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的水平,原来的人地关系就可能不适应反而阻碍了土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考虑土地的特性,为了稳定,我们给予合同的期限是几十年不变的承诺。(插一句:这使得家庭人口变化无法及时反应到土地上,不管你现在家里多少人,“分地”就是按照当年你家的实际人口,至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就无法调整了)。我们知道量变引发质变(还有外力的引导)的规律,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快就开始变,这是当时我们的视野和思维所料不及。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生产要素中人的因素弱化了,严重弱化了,农业技术及其管理方式在生产中的作用取代了劳动力自身耕作技能的位置。
从生产的角度,要求分散的土地进行集中管理,统一调度,才能提高生产效率,简称最好收回。从社会的角度,借钱容易讨钱难,“高高兴兴借你钱,吵吵闹闹还你钱”,当年给予他人土地,他们“感恩”的情感属于一次性用品,没有理由今天你要收回,人家还高高兴兴!大家似乎都看到这种情感差异,“坏人”的代价太大,大家都畏惧,简称不好收回。从政策的角度,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合同行为,而且现在专家也给他冠上了制度的帽子,就不是那么容易更改,也不是谁敢更改,简称不能收回。
于是,在这些背景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户(那是切肤之痛啊)对比代表集体利益的某法人代表(那是隔靴搔痒啊),在土地纠纷面前会有更直接、更强硬的态度。契约就变成一个政策的表现形式,所以在承包经营权证上第六条:“因国家和乡村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或使用土地的,发包方有权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成一句大家都没有理会的话,十分默契。在农户的眼里,他们拿到的是政策,不是合同,所以没有违约条款说明:如果农户不给,集体可以采用什么强制办法?只要农户不愿意,他单方面就可以不管什么合同。这个遗漏对征地者来说,到底是束缚还是放宽?或者就只能取决于决策者的级别和决心。
反过来说,农户为什么会愿意接受土地被征回?或是农户有更好的经济来源,转变了个人的求生方式,土地本身对他没有什么用了;或是对于土地的补偿金比较满意:满意于自己的心里价位,满意于获取比周边人更好更高的补偿组合;或是迫于舆论压力,尤其在公益项目,不想因为一点钱而坏了自己的名声。或者还有其他,但不管什么理由就是没有“合同”(应该是权证了)什么事。
那农户为什么不愿意?当然主要是因为钱,认为不够多、认为还可以更多。而且如果他战胜了舆论压力,心里上过了关,在征地面前基本就无敌了,不是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而是说“我是光脚我怕谁?”当然,还有一些理由,比如:情结,情土地结;斗气,斗存在感。
2、名义的公家,意识的私家。
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只有国家和集体,哪里有个人的土地?但是这个观念在农村的思想基础不够牢固。几千年私有化概念渗透到农村的每一道文化礼仪,表现在什么事情都要区分是你的或我的,你们的或我们的,谁先谁后,连亲戚都是三代五代分间疏。农户会为了一条排水沟,一寸土地打的头破血流,因为意识里私我的概念一直支撑着斗争毅力,这时是不会管我们说这些土地都是集体的。明明是人家借给你的东西,但是你什么用也不说,用坏了也不说,丢了,仍了也不说,好像开始就没有打算还!意识里就当做自己的财产来支配。
一是土地使用随意性。土地租借给你,是让你种粮食,让它生产出果实,为社会创造财富(粮食安全)。水稻、大豆等主粮还好,水果蔬菜也就罢了,有些地方种上几颗果树不管理,甚至荒着种草,就是为了占着位置。我自己能喂饱自己,谁又会去管谁?我有时候会有一丝寒意:农村的农民现在也去超市买米吃。或者这是经济学家高兴的事?还是社会学家悲痛的事?
二是土地交易随意性。奔着“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的原则,土地隐形的假自由市场往往使得交易价格高于政府的指导价--否则人家为什么要买给你?于是在国家集体需要征收的时候,包括旁边的地皮就要参照最高的交易价格,甚至取最高值上更高一点(因为你是公家,这个便宜不占好像对不起自己的人生)。这个有点像股票操作那样,通过交易抬高了地价。但是,他又不是完全市场,因为在农民之间,大家都有地,生成不了足够多的“买方”。然后国家和集体来了,就这个铁定的“买方”因为不得不买的背景下也没有自由,事情就复杂了。私下交易还直接影响着土地数据的管理,土地承租人的信息变更并没有及时体现在土地管理者的手里。农户之间的契约(字据)干扰了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契约,那么国家集体征用的时候,补偿款应该给予谁?按照原来合同给的张三,还是目前“真实”的李四?
三是土地破坏随意性。发现一些土地被流转(也是农户之间自信组织,按照年度收租金)后,种植大户自然将经济效益做为首要目标,那就不管土地的长久寿命以及农作物生产的可持续性。(插播一个玩笑:人家房东给你房子不收租金了,但是你作为二房东不住了,租出去了却要收取房租,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别人借给你,那名义上是别人的东西,但是用起来,十分任性。科技改变生产力,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产量,这些是今天眼前产生的效果,但是科技似乎潜在破坏了土壤结构。技术能迅速推广,说明门槛比较低,许多农民很快都会用,喷喷洒洒下,植物吸收不了的化肥、农药,留给大地,大地吸收不了,就留给雨水,雨水到河里,那接下来就是大家一起爽。大地母亲现在就老得快,土壤无法回到原来的模式,就像吸毒一样只能一直靠着科技走科技这条路。举个例子,经济林对山体的破坏可以用桉树来说明,这一外来植物强大的生命力一下子改变了原来小地区的植被环境,“抽水抽肥”使用的特定肥料,据说还有其落叶对其他物种的毒杀等等,就算以后不种了,也不知道要几年才能恢复原来山体最初的活力。
3、生存是形式,投机是实质。
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逐渐成为许多领域发展的共同要求。而且,随着经济的跨越发展,土地作为虚缺资源,其价值增长的加速度明显领跑其他资源。不管是用于居住的房屋,还是用于生产的耕地,在我村民的淳朴心里,征地拆迁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理想的道路,几乎稳赚不赔,差别只是赚多少而已,十分像最近股市里抽到新股的签。虽然由于情感等原因,难免会有个体出现征迁的纠纷,但农户整体的思想还是偏向于拆迁。一个“拆二代”的名字能城市夜生活占有一席之地也不是随便得来的。在经济利益(货币)的驱使下,投机的心里促使土地转变了它原来的性质。
在农村,原来所做的一切的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生活质量。比如,人们想尽办法,大家出钱,集资修道路,为了居住条件更好;筹劳修水利,为了耕地的生产条件更好。但是现在这个思路变了,大家闷头在家做的许多事情或许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助。首先是盖房子,没有新房子也要加高楼房,增加层次就是增加建筑面积,这是一个很良性的指标,至于里面装修配套后面再说。农家的院子是原本是孩童玩耍的主要舞台,是乡愁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现在也一直再减少,似乎要被历史收回去了。因为一个很奇怪的补偿标准,裸面土地几乎没有补偿(因为在法律上,土地是国家的,补偿金极低),重点是土地上面的建筑物,属于居住者的财产,才能获得补偿。所以能搭的地建起来才有价值,管你赔不赔?什么航拍不航拍?至少是一个机会,后面谈判啊,“斗争”啊什么的总得有个理由用来发力。
在祖宗的眼里,房屋建设是为了遮风避雨,是为了居住舒适,所以才有那么多如位置、形状、格局等建筑文化。但现在这个不重要了,伟大的“建筑面积”这个指标独得恩宠。于是一些新的房子占地建成五边形、六边形我认了,那个三角形算什么?为了几何稳定!你的数学老师这么忙,还要客串教建筑?
说的极端一点(夸张了):我今天“忍辱偷生”,可以住的憋屈一点,为了以后的“薄积厚发”。“吃的苦中苦,才能赚的钱上钱”。
道理归道理,补偿顺利了还好办,怕的是“反道理”,一旦某天发现我长久的憋屈没有换来理想的回报,那就是思想包袱。所以一旦补偿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标准(当然,也可能没有数字标准,标准就是“多多益善”),前面的投入和忍受就容易变成愤怒,都要“反抗”。对于那些几乎用一辈子的耐心来等待时代机遇的善良淳朴人们,我们不要随便怀疑他们将为此投入的决心和勇气。个体的善良禁不住利益的考验,集体的善良更禁不住漏洞的引诱。对于一些普通农民,好像真是一种理想的发家致富之路。
媒体和网民的看客心里,造出的舆论鼓动,把个别抗拆“勇士”塑造英雄的角色,似乎也给后来者打了鸡血。好在现在这个社会也开始逐步理智看待,不明真相的群众吃上了西瓜后,有许多是懂装不懂。
二、你方唱罢我等台
中国几千年的正史几乎都是发生在城市的文章,让秀才进士们难于想象到的是,今天的农村也开始有故事了。经济学家的歌声唱到了农村,不一定好听,但是嗓门很粗。农民沸腾起来了,但是幸福来得太快,农民兄弟作为群众演员还没有穿好服装,唯有的道具是土地,跟着吼,声音太大,破坏了农村的安宁静谧。
1、科技释放土地存量,经济提升土地价值。
有需求也有供给,这才是水到渠成的故事。一边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地地地,越多越好,比如说房地产要开发高档住宅小区、精品写字楼,比如说工业区集中建设提升管理,捆绑前进。一边是土地供给,比如,居民区的拆迁安置,比如说耕地山地的用途转变。两者牵线搭桥的中介有很多,其中,科技是关于农村供给土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农业科技提升了土地单位面积的生产效率(产量),尤其是水果蔬菜。在科学的品种培育、种植管理、采摘保存等技术背景下,产量惊人不说,质量也再惊你一次人。在盛产西瓜的季节,我们的农户推介他们自己种的西瓜,主要的卖点是用农家肥,没有膨大剂、催熟剂,纯“手工工艺”。那价格贵了一倍也不算什么(一斤2.5元我们没有意见),毕竟人家产量不高,但当我切开的时候就麻烦了,不红就色不美,不甜就味不甘。于是我就犹豫了:我成年人就没有什么过早发育的事,什么激素抗生素在舌尖的诱惑下,我可能选择站队科技。那外来一卡车一卡车的西瓜摊确实有市场竞争力。
听说,生产更多更甜的西瓜居然只要更少的土地(贫瘠),那么供给“民以食为天”的土地在数学计算就有多出来的感觉。这是关于农村的能“生出土地”的故事。
既然有了剩余产品(土地),就面临怎么分配的问题。
第一产业是农业,是最初的土地主人,就说水稻,亩产斤,一年两季,算多少,买到元左右,利润元,科技来了,好吧,利润算你元。第二产业是工业,他找到农业商量,说我一年给你元,你不用干活,坐着数钱。第三产业是服务业,他说给你元,你也不要干活,坐着数站着数都可以。房地产,说,呵呵。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土地公公在孙大圣面前还有什么好说的?经济说“我需要你”,农村说“我有了”,看似他好我也好的局面。但这不一定是双赢,反而可能是矛盾。因为没有标准,信息不对称,利益会打破平衡。
强盗内讧主要是分赃不均,至少他们各自认为自己被不均。
2、农民富裕要求更多土地支配。
赚钱就会有钱,有钱的目的就是享受钱能带来的福利,比如更好的衣食住行,然后是伴随着你脱颖而出造就的无形地位,或许还有很多。
在农村,金钱财富的主要表现在于住,也就盖房子。盖更多的房子、更大的房子、更漂亮的房子,首先都需要土地。一从信仰来说,盖房子是对祖宗基业的继承。世代居住在农村的农民,祖宗基业就是一代一代的继承,房子老了,再翻新,那里还有风水等命脉说人丁兴旺。耕地的作用有吃,房子的作用有住,后面你才有机会悠闲的在树下河边聊天。二从文化来说,盖房子是对财富价值标准的理解。原来农村社会秩序里面辈分可以作为第一要素,但是今天到处讲平等的风刮到了农村,农民们之间的内心对比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富欺贫,贵欺贱”不是说在法律地位上,而是在农村文化,也不是说像地主恶霸那样欺凌,而是话语权之类关乎非政治权力的范畴。比如过节庆典、祭祀等,你出不起钱就说不上话,谁知道你有钱?房子说话,钢筋水泥是硬邦邦的铁证!三从家业来说,盖房子是对媒妁婚姻的理解和顺从。孩子长大了要成家,这是农村的头等大事,说门当户对自不必说。你离开自由恋爱市场,到了农村媒婆手里,家里有没有房子,可是一道硬菜!你有多少钱,是你自己还是别人的?我看不见,但是固定资产就固定在那里,所以许多时候,农民借钱也要先把房子盖起来,不筑巢就引不到凤。四从经济来说,盖房子是对土地利益的预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有的事情,长久这么重复就会变成祖宗的思维,形成习惯传下来。比如开荒就很有特点,早期开荒靠什么,首先是勤劳,然后什么证明荒地是你的?种上植物,就像插了旗帜标杆,这就是你开的慌,你的地。现在土地的使用用途被政府界定了,荒地是没有了,但是思想还在,开拓进取,于是可用的地还是盖起来安心,也是相当于插上你的标杆。
除了住房外还有生产,农村手工小作坊现在也十分常见,我们暂且不能去说土地被他们使用的效率是高是低?,造成的环境破坏在哪里?至少反应在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数字就要增加。
农村的公共建设也来了,道路是最基本的,越来越宽,越修越长,交通网络越来越完善;还有公共的设施,比如文化中心,校园等都要相应的提高,这些对土地的需求数量也十分惊人,而且位置要比较好。
说到这里,从这个角度要对乡镇干部说一声辛苦了,要不是他们一直在高压的贯彻着对违章搭盖、违规用地的黑脸红脸,农村早就没有多少可耕作的土地。
3、土地政策利益多方博弈。
以前孩子多,家里要是有什么零食,水果什么的,家长随便往桌子上一扔,大伙就会马上冲过去,虽说不一定抢,但是至少名分要凑上去,见者有份。
现在农村土地值钱了,也开始了多方的利益博弈。大家都希望来分一杯羹。政府来了,代表国家,名正言顺因为土地国有,但是也为难,因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何况多少年来农民就一直守候着它。
(开发者也来了,“你们不要吵,我来做蛋糕。”
“我们可以不吵,但是你不能叫我们走开啊,面粉是我的!”
“蛋糕你就不要想,面粉我买!”
“不卖!”
“干”)
利益,谁不要?钱,谁都缺。
比如财政,那是政府的命脉,土地财政一个热词。但政府的顾忌很多,既要当前利益,也要考虑项目后续利益,农村的土地很多都是国家基础设施的项目:铁路公路、水利码头等,如生产工具一样,地方政府的直接获利不多,往往都是通过其促进其他产业发展后产生效益。压力可能来于上级,要求项目有进度,按时或提前完成;压力也可能来自于底层,要求补偿的花样很多,还有稳定的考核指标,双压下动作就容易出格。
农民需要利益,利益最大化。实在的人就认可政府,接受政府的标准。麻烦一点的人,如果心里目标是一个具体切实的数据,钱够了就可以。麻烦二点的人的标准是“别人不能比我多”,土地什么区别我不管,项目什么标准我不管,在我们这里就都是土地,最好是我的补偿标准都比别人高。
项目开发者,生意人,能赚不能赚,钱是算好了,但是意外的事情最怕,咱和政府讲法律,讲规矩,讲程序,什么都办好了(至于什么办是另说),可是要开工的时候,为什么来了一个要躺在推土机面前?在农民的眼里,开发商和政府没有什么区别?答应了也可以反悔,或者因为发现被骗!于是开发商就容易激动!
那就这三方吗?不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是看戏不嫌事大的第四方,项目身边的人,我们农民兄弟的兄弟,那些人负责出主意,那边可能两败俱伤的后果也不会影响他好心人的样子。然后是热心的曝光者,也可以是记者,用客观的正义报道主观的事实。然后是义愤填膺的热心网民,配合的几乎和预料的一模一样的。
于是在土地这个问题上,好像没有参与的都是好人,参与的都是贪官、奸商和刁民。
三、求为而无为,有为则乱为
(此处略去个字:比较敏感,怕误导别人,所以略了去,敬请谅解)
(预告:下一期我准备汇报,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