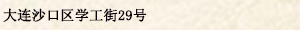农家乐包菜第四道贫困
这是一个热门的词汇。政府经过统筹考虑后,计划在年实现全国脱贫。各地响应着,把他当做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为了按时或者提前脱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是一个广泛的理论。许多学者调研研究出成千上万的论文,培养硕士博士。但这里,我只从自己的经历说事情,管中窥豹,表达一隅之惑。
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培养出大学生的农户可能是个富裕的家庭。在城市安身立命后,亲戚共了楼房的首付,然后你通过努力终于过上了清贫的还贷生涯。
应题之意,实际包括三个字,贫、穷、困:贫是上下结构,分和贝,贝即是钱的意思,本属于你的钱被分走,所以贫;穷也是上下结构,穴和力,在洞里面有力使不出来,是赚钱无门,所以穷;困是内外结构,口含木,味同爵蜡,有口难言的滋味,所以困。
一、贫困不再是皮包骨
一所学校,如果不是刻意挑选组成尖子班,正常情况下每个班的学生总会有些学习好,有些学习上不去。补习是一个办法,但不能包治百病。只要有考试,就会有伤害(名次)。
从学校到社会,贫困求致富的道路也是如此。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贫困几乎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破房子破衣服的印象,但这个画面现在渐渐不适用了,因为今天的贫困只是富裕的副产品。对比隔壁暴发户天天下馆子吃鲍鱼,我这骨头汤就花蛤就算贫困的委屈,但是对比自己十年前对着榨菜蛋汤那就是富裕,对比三十年前吃个干饭都让人羡慕的窘迫,那现在就是炸天了!
从物质文明角度看,今日的农村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不同于城市支撑“繁华”的代价,农村生活成本的“起步价”比较低,如果农户要求不高,日常吃、住、行的花费就更少。
吃,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问题。农民有田地种植粮食,有园地种植蔬菜,家门口还养鸡鸭等家禽。政府在农业税取消之后很少干预这些农事活动,所以农户完全有条件自给自足。现在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有一半的农村人涌向城市,吃着城市由大农业基地运来的大米和蔬菜,另一半留守的农村人也不再热衷于种田,或许流转、或许种果树、或许抛荒,最终也会选择去买米吃。所以吃是可以保障的,即使是最贫困的家庭,也有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无非是吃的好坏有差别。但自己的菜桌,只有自己知道吃的好不好,没有相互之间的直接对比,农户就不会太在意。
住,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房子的好坏大家都看的见,容易自然形成相互之间的对比,大家不一定要说,但是心里都明白。住的类型有多种:有些人住着祖上留下来的老屋子,古朴温暖;有些人选择新盖一幢高楼瓷壁,十分耀眼。老屋子也不是贬义词,只要有人持续住,房子的寿命会很长,遮风避雨的效果一点不差,还可能冬暖夏凉。许多老人会选择住在老屋子里,不是说他家有多穷,实际上他们也盖了新房,但是他(她)不愿意和儿女住在一起。只有三代(人)以上都挤在一栋老屋子的时候,这个老屋的破旧狭小、昏暗阴凉、交通不便才会变成现实贫穷的问题。
行,几乎是一个“多余”的问题。政府根据公路等级要求建设了国道、县道后,乡村道路几乎全部打通,道路的网状结构如血管一样渗透每个行政村。农村的出行不再困难,有路就有车,好的自己买车,轿车、摩托车,差一点的可以选择做班车。天堑变通途,出行的目的地都可以达到。纠结出现在出行工具的区别演变成了各家财富的表现,尤其在婚姻媒介的时候,车子成了房子之外的第二个显性指标,对比会让贫困产生压力。
1、农村是贫大于穷
为了发展,我们设计农村为自治的群体部落,但是自治也不是完全自治。农业要收税,农民被限制(自由流动),优质人才等各类资源持续供给给城市,所以建国几十年农村的基本面貌没有多大变化。到了近三十年,我们的经济跨越了瓶颈期,量变到质变,农村开始进入建设序列。原来的“付出”开始换来回报,教育、交通、饮水、电网等基本的生活设施不断获得国家投入,改善了农村的整体面貌。农村的发展有政策保障,农民可以离开农村外出务工,带回财富建设自己的家园。如果你想致富,有工可做,有路可选,你的力气使的出来,这都不再是“穷”这个字。但是基于自治的制度下的影响,许多农村发展项目还存在程序的制约,比如农村要通过自己的渠道到各个政府部门争取资金项目,提升居住环境,这容易造成农村之间的参差不齐,有的已经美丽了,有的还在落后。这种“贫”的思维还在继续,许多“优惠”没有能力覆盖所有农村,所以给予平台,让他们各显神通,让一部分农村先美起来。(过去是先让城市美起来)
如果农村哪条道路坏了,或者是要扩建修复,这个村子的人就要自己去争取,去筹资;如果城市的哪条路坏了,周边的居民无需劳累,会有相应的部门去维修,去改造,白改黑,时间快、质量好。
2、农民是困大于贫
农民群体里,似乎有一种纯朴的思维:在家族里,在村庄里,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固然重要,但是更希望在熟人社会里受到尊重和认可,自己的面子,自己说出的话,要有分量。这不是权,是威——威望,或者是话语权。他们很少去研究自己的农村为什么会贫穷,因为在他们眼里农村本就是贫穷落后,没有什么好抱怨。他们的焦点是在农村里互相的对比和自身的“地位”。
农村自治是基于农村宗族文化建立起来,是宗族权力的制衡衍生,没有大家族的背景很难担任村干部,无法做好具体事务。原来大家的经济差不多,宗族文化主要参照辈分:小媳妇会受气,但是媳妇可以慢慢熬成婆,总有一天会接管比赛。但是今天,金钱犹如这个规则的外来事物,它逐步被社会认可,致富者慢慢形成了新的“阶层”,打破了农村原来话语权“潜规则”的平衡。那些贫困农户好不容易熬出辈分资格,却发现规则变了,婆婆的身份不再管用,财富阶层插队直接进入农村的话语层,抢走了话筒。这使得贫穷十分困惑,富人并没有哪里做错了,并非不按套路出牌,只是套路变了,这种委屈说不出来。比如祭祖拜神,原来大家财富差不多,在礼节程序上,辈分者主持全局,现在游戏被金钱打乱了,有钱人赞助个几万块,许多规矩就被修改了——菩萨巡游的路线都可以变,所以一个节日下来,有钱人的威望就涨了一节,直接登上台面。
贫穷,在脱离了温饱边界后,不在是贫穷者的最大危害,由贫穷造成的次生伤害(地位及依附)才是最大的隐患。
3、村集体是又贫又穷又困
村集体,就是村委会,村务工作的总负责机构。全国很多村庄,平原、沿海、山区,各有各自的特点,但他们最初都有一定的集体资源。村村有本难念的经,在各自的自身或外界的干预发展后,有些村的资源得到保护,并且继续发展,形成了村有集体经济,但对于大多数的村庄来说,他们的集体资源被“私有化”,村级财政收入基本归零(不欠账就算好)。于是,村庄便将目光转向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项目(不管哪一种项目总是有项目工作经费)。因为村一级属于自治,没有明确的财政保障,没有统一标准,所以项目争取就存在相互差异,各个村依靠各自的人脉资源,遇到丰年丰收多做事,欠年欠收少折腾。
对于大多数没有稳定收入的村庄来说,管理或者服务着最广大的人群,就没有经费保障。但是,村庄又是一级机构,承担着许多政策的终端落实。许多政府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制定的“惠民惠农”政策最终要依靠农村集体的具体工作来实现。这些政策不管实际不实际,各部门都认为自己出钱了,“拿钱送你还有什么不好的?”,那效果在政策计划中就预测好了。所以没有实现好就是基层重视不够,那就要督促,层层督促最终这个压力就转到了村集体。村集体没有权力,没有资金,村干部将只能消费威望去实行,这是村集体的困境。
没有财政保障谓之贫,没有集体收入谓之穷,没有执法权力谓之困。
(关于村集体,将在《自治》一道独立报告)
二、贫困不都是老实人
1、群体的组成。一花一形状,一人一故事。贫困的人群(贫富差距的形成)有着一样的贫困状态,但总有各自的原因,或者从不同的道路走来,或者是同一条道路,却摔了不一样的跤。
◆游戏规则的筛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完全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但是农村人口太多了,许多时候,我们把马松了缰才知道是野马。在法律和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时代,那些提早解放思想、勇于冒险、敢于拼搏的一批人开始尝试、冒险、投机各个领域门路,寻找赚钱机会。“除了死外,什么都要趁早”的血腥故事造就第一批致富者。反过来那些赶不上“早”的,成为走向成功路上的失败者,成了第一种贫困者。游戏比赛总有最后一名,总有淘汰者,遗憾的牺牲品。
举个极端例子,比如说制造假冒伪劣。第一个人借了50万,开始干,第一年就赚了50万;于是第二年,就有3个人开始这样干,也去借了钱,这是时候你开始犹豫,你在害怕,结果最终,这3个人各赚了40万;第三年,你终于决定了(一批这样的你决定),于是就有10个人这样干,借钱开始,但是刚到了半年,政府出手整治了,没收、罚款、判刑等,结果大家不但没有赚钱,还把借来的本亏了!最后盘算一下:第一个人还有几十万,第二批人还有几万吧,数第三批最惨,你的家庭倒欠几十万,不是银行,是民间借贷,财富和名誉的高利息。农户从此就开始分化,“一将功成白骨枯”(没那么严重,但是道理一样)。例子可以不用这么极端,但是第一桶金和第一坑井确实是并存的,并持续影响以后的各自发展。“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意外事故的影响。如果游戏规则有投机倒把的成分,那正常的生意也有成败的结局,踏踏实实做生意,同样存在着风险。比如承包流转土地,种植蔬菜,去年不错,今年不错,辛苦一点,钱还是能赚一些,但是明年呢?谁能保证年风调雨顺,生意兴隆?动植物本身的疾病、成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台风等极端气候的影响、政府的监管起伏(农残等),哪一个不确定因素都可能造成血本无归。农户的家庭资金结构十分脆弱,生意允许失败,但是不能允许第一次失败。第一次失败造成财富和名誉的透支,容易持续贫困。
还有一种意外是身体意外,如伤残、疾病等。这种意外可能直接吞噬了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甚至由正值变成负值成为家庭负担。原来依靠勤劳的打工型家庭就容易从此进入贫困序列。
◆个体差异的结局。按照正态分布理论,个体差异到可以影响结局的都是边缘一小部分人,大概就只有5%(具体数字记不住了),就是说人里面,特别优秀和特别不优秀的大概各自只有5人左右。5个优秀不用当心,老师喜欢、领导喜欢,随随便便就是奔小康了。但不优秀的5个人,很可能就是贫困的人群。5个人不多,沿海省份的村庄能被政府界定贫困人口也就5%-10%。换句话说,他们是政府界定贫困人群的主力军。第一类是身体残疾,天生的残疾,包括智力。他们从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就被确定,所以大家对其帮忙(培养)便有一个基本定位。在农村,他们先天条件本来就比不过正常人,后天可能又接受比正常人差的教育培训,所以极易形成贫困。一个可怕的现实在农村中形成: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残疾,就会有几个残疾,是遗传也是婚姻。残疾人通常只能找残疾人做对象。于是贫穷者周围的亲人也是贫穷者,这就失去了亲朋好友互相提携发展致富的机会。第二类是意识残疾,不踏实地,总是好高骛远,或者极度自尊,两种极端。比如懒汉,在他的意识里没有正常荣辱观,得过且过的日子,总想着一夜暴富(也不排除有些人是看破人生,完成自我超越)。还有比较可悲的意识残疾:太好胜,明明技不如人(至少目前)却死不服输,“再苦不能苦面子,再穷不能穷形式”。自己生活不好可以忍受,但婚丧嫁娶,祭祀拜祖这些对外礼节就是借钱也要辉煌隆重,供养子女要上贵族学校(专科不上,要去昂贵的三本),治病医院。
所谓的“因学致贫”应该是一个因果的逆向理论。一个家庭可能因为贫穷,让孩子赶紧去打工赚钱,这是辍学,叫“因贫辍学”。教育部门现在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不收费,哪里会有一个因为想发展去拜师学艺然后拜成贫困了?那还不如就在家里不去念书,还不贫困。
2、贫困的思想。有一种冷叫妈妈觉的你冷,所以妈妈会要求你多穿一件衣服。作为妈妈,看到你添了衣服,她的心里顺了,不堵了;作为儿女,可能真的冷,那妈妈很温暖,如果并不冷,那妈妈很啰嗦;作为卖衣服的商贩,最好能借些鸡汤的故事多卖几件衣服。
事情总是有利弊。如果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饥饿的眼神,那你给他0元钱救助,他很感谢你!如果你在天桥上说谁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就可以在你这里领取0元钱,那么就有许多人会去换一件破衣服、化装整容,甚至给你一个更加哀怨的眼神。
这是因果正向逆向的两端。
所以政府在想,是时候了要消除贫困了。政府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必要,让发展的福利覆盖最广大的人民,但执行起来有许多制约。如同妈妈看到隔壁的小孩受冻,就回来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加衣服,至于加多少,加多厚,妈妈们研究一下就定了标准,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要穿。这样的妈妈给我们的感觉不对,因为如果我想要衣服,我就说自己是那个标准范围,如果那个衣服不好看,我就说自己不属于那个标准。作为政策,这是天生的不足,一种普发性的要求,而不是个体性的请求,所以一个标准,对应一群人,造成了几家欢乐几家愁。
所以基层在想,这是一道惠民政策,是一个好事,有利可图的事要去争取。先把名额弄到,你要怎样的标准,我就给你怎样的标准(不要误会,我说的不是造假,而是造真,这个将在《自治》里面说),我甚至可以不断努力达到你要求的标准。然后政策来的时候,我可以把政策先落实到同样满足条件的一部人,或同样不满足条件的一部分人,拿着妹妹的照片给姐姐征婚。贫困变成了一种资源。但现在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后续的影响,比如农户开始争夺贫困的帽子引发的纠纷,让基层也不愿意掌握这个资源。
所以贫民(农民)在想,政府要来帮忙了,我需要钱,还需要其他的东西,这个时候都可以提出来——我的春天来了。政府肯定是好的,越高层越好,如果我对比别的贫困户有不一样的补助,尤其是比他少,那就是村干部故意在搞差别,就是看不起我,就是利用我来欺骗政府。一个贫困户的眼里,政府最好直接给钱给物,补钱,持续的补钱,给我介绍工作、教我养殖技术等等没有什么必要,不需要你们政府。至于发展,真想自己赚钱的话,农户最相信的还是亲戚朋友,跟着亲朋好友一起去打工更直接,更值得信赖。政府一会儿提倡养猪(补贴),一会儿又禁止养猪的故事才刚刚过去不久。他们不大相信政府说的帮助,因为政府看不见,这几个官员和村干部就是一切,可是他们不可信任:经常变卦,位置不变人员变,或者人员不变政策变。
三、贫困不该是大灰狼
贫困是一个历史书籍共同面对的问题。我没有专门的研究这些历史,本文在这里就这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发展阶段讲述自己特定的担忧。
1、差距大不大?农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财产(不动产)通常是显性,喜欢对比优势,其财富(钱)却又喜欢隐藏,“财不露眼”大概是怕贼惦记。农户收入基本无机可查,所以我们很容易知道哪户人家有钱,却很难知道到底有多少钱?村民们都是在互相交谈、互相推论、互相吹捧中排出自己村庄的福布斯。如果是账面资金比数字就好说明,最有钱的个体或最有钱的群体(top10)到底占比了全村多少财富,与贫穷(按照零财富算,不包括做生意的起落破产)的差距是多少?但这种对比在农村没有意义。
差距(别)体现在前面说的次生伤害。农村的贫富差距影响着农户之间生活空间的相互挤压。和城市不一样,农村是熟人社会,人员结构相对稳定,社会活动比较集中。所以关于贫富造成的差别不能单纯对比财富,而是全方位的对比。富裕者房屋有多大多高?在风水上压制了邻居的程度多少(许多内涝都是人祸)?富者在村中活动的话语权有多大分量?富裕者说了句,贫困者会不会有10句,等等。这个差距是不是在继续拉大?是不是形成除了血缘关系外的第二种阶层分化——有钱开始和有钱人玩,贫困者和贫困者互相抱怨,这种分层会对农村文化、政治形成新的冲击。
2、道路通不通?致富应该有也必须有先后关系,就像两条腿走路,总要有一条先迈出去。任何一个开放的平台,最简单如同考试,都会形成名次先后,有人学的快,有人学的慢,所以没有必要对此抱怨,这是自然的规律。但担心的问题是先富后富到底要多少年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先十年二十年,一代人可以,如果先个几百年,几代人那就不是先后的问题。考试的事情,落后的学生可以通过更加勤奋、补课等实现成绩进步,大家都考一百分(或者都过了及格线,拿到证书),好成绩的学生如果不学习了,自然也就退步了,说明考试这个开放平台相对公平,能上能下,沟通上下的道路是通的。如果那些贫穷者,几代人持续努力都无法致富,而另一边富二代三代持续下去,说明沟通贫富这条道路是狭窄的,或者不通畅。
个农户每年他们的财富都会有出入,但是上面的10名,中间的80名,后面的10名,这三个阶层的农户常常只在本阶层中流动,很难出现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为什么?因为农户的谋生方式基本被固定,上面10户的收入渠道很多,城市有店面、房产,自己还有稳定的生意圈子。除非他想进入城市前10名才会去冒险投资,否则农户的保守会稳定已有的富足。中间阶层也有稳定的收入,家庭就业劳力充足,没有历史包袱。底层的10户一般自身的劳力水平偏低,眼光保守等,通常家里还有病人、残疾等历史包袱,所以很难改观。
3、心情平不平?整个社会发展的高节奏,几乎让每个位置的人都在抱怨。社会制度给予了个体的尊重和自由,容易让个体夸大自身的存在价值,抱怨社会给予自我认可不足。这些问题在一个农村社会里有点区别,上述后面10户的人,财富水平最低,但是出人预料,他们很少对社会抱怨,或者抱怨也仅是针对某个村干部的具体行为。而且,政府实施低保、扶贫等政策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考虑自身的特点,他们更多对政府心存感激。上述上面的10户的人家,他们是改革利益的既得者。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如果失败了也没有人帮忙买单,属于后果自负。但是他们的经历影响观念,比较通情达理,对社会的认识角度比较全面,没有那么多抱怨。心里的抱怨主要集中在中间那80户的一部分人,他们有些人一样奋斗过但是没有进入前10,便怀疑是自己受到不公平才输;有些人出去打工,见过世间富华,资本权贵,埋怨自己出身劣势;有些人不敢冒险,又眼红他人暴富,有人眼高手低,好逸恶劳。(感觉政府应该把自己一样纳入扶贫范畴)。
内心的不平衡会表现到村中的具体事务。他们上不去,无法取得财富话语权(村委需要家族长久人气积累、更加不易取得),又不肯如贫困者倾听接受他人意见,夹在中间“受气”就容易想“出气”。所以哪怕是公益事业,不同的声音总是在这个阶层发出来,只要触碰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就会借机漫天要价,强行体现存在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