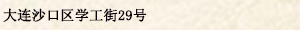流年童年的那个菜橱
每当我把还飘着诱人香味的各色菜肴,倒进垃圾桶时,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时的那个菜橱。
童年里的一日三餐再简单不过的了,早餐、晚餐是稀饭,配稀饭的常常是萝卜干、芥菜梗,如果炒萝卜干时能放上一个蛋,煮芥菜梗时能放几条小鱼,那对我们来说无疑就是美味佳肴了。很多时候,妈妈只是从瓮里掏出几条萝卜干或者芥菜梗,洗净,往盆里一放,就算我们两、三天配稀饭的菜了。
只有中午才有机会吃到干饭。配干饭的菜,也是极其简单的,往往都是自家种的丝瓜、葫芦,或者高丽菜、空心菜,反正地里种什么就吃什么。记得夏天常常是丝瓜煮汤,素炒空心菜,冬天就一直炒高丽菜,煮萝卜汤。有时一连十天半个月都吃同一样菜,我们也一样吃的津津有味,毕竟能吃干饭,就有炒菜,有炒菜就有一点鱼腥,这对于成长中的时时饥饿着的肠胃,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慰籍了。
看起来似乎没必要菜橱了,吃都吃不够了,哪还有剩菜放进菜橱呢!可就是那么巧,我们家有棵树被台风刮倒了,又凑巧有个参军回来的邻居,刚学会了木工,想练练身手,于是父亲和那小伙子就一拍即合,请他用那棵树做一个菜橱,工钱是10元人民币。
那小师傅带着工具在我家,又是刨,又是锯,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星期,终于大功告成,一个漂亮的菜橱呈现在我们面前。主体部分的两扇门还加了尼龙纱,以防蝇虫、蟑螂,这门还能上锁,以防老鼠和猫狗闯入。菜橱最上面的一格,可以放锅、缸等大件东西,下面是两个抽屉,最下面的一格摆放碗筷。
那两个抽屉,我和妹妹一人分一个,我是右边的那一个。记得有一次,外婆给我了几个红艳艳的荔枝,我剥开吃了一个,那鲜美的甜味简直让我太惊喜了,我再也舍不得吃第二个,于是小心翼翼收藏在抽屉里,想留给下地干活的妈妈吃。可说我后来居然把这事忘了,直到好几天后不经意拉开抽屉一看,那几个原本鲜艳欲滴的荔枝,早就变成干枯暗淡,皮也烂了,一碰便流出浓浓的酸臭味来。那一刻我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懊悔!
身为家中老大,我很早就能独挡一面了,放学一回到家,就开始提水,做饭,喂猪,农忙时父母在田里加班时,我还把饭菜提到田里去,然后回家把剩下的饭菜分成三份,打发两个妹妹就餐。记得那时配稀饭的菜都做得很咸,一餐饭常常配不了几个菜,大概是没时间经常做菜吧,妈妈每次都做很多,所以,没吃完的菜就放进菜橱里,下一餐拿出来继续吃。
菜橱里还放着做菜用的油。那时偶尔父亲会买回猪油,下锅炸好了,盛在一个小盆里,第二天就变成白白的固体了,用汤勺挖一小勺,就够炒一个菜了。父亲用油很节省,所以每炸一次油,就可以撑好长一段时间。
有次,父亲一时兴起,非常慷慨地挖一勺猪油,给我们姐妹碗中的包菜咸饭各加了一点,那白花花的猪油在热饭里慢慢融化,诱人的肉香阵阵飘起,那餐饭,吃得我酣畅淋漓、那滋味至今难忘。
此后的几天,我都偷偷地打开菜橱,偷偷地用汤勺挖一点猪油,埋进咸饭里,然后裹着自责与罪恶,大口大口地嚼着。直到有一天,父亲端详着那盆猪油,疑惑地自言自语:这次猪油怎么用得这么快?知道那天之后,我再也不敢偷吃猪油了。
后来,农村经济好转了,我们家也有了冰箱。这个菜橱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我们家的厨房重地,被妈妈放在另一个屋的角落里,连同那些淘汰掉的锅碗瓢盆一起,默默相守着,守着那一段忍饥挨饿的岁月。
/8/20
柯月霞,笔名六月雨荷,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爱阅读,爱旅游,渴望凭着文字,与你,与世界自如地交流。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优雅》、《一杯茶的幸福》、《最美的时光在路上》,厦门女作家合集《遇见》
老家旧事忆不完
赞赏
人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