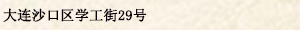田间地头,那些渐行渐远的动词
父母均入古稀之年,身体还算健朗,守着三分地的菜园,两亩左右的水田和旱地。尤其是父亲,退休之后像是入了魔,不仅经营着自家的田园,还将别人抛荒的旱地精耕细作,每天劳作时间超过八个小时。即使去县城办点事,基本当天来回,哥哥、妹妹想留其住一晚都困难。
我到家时已近中午,父母到村口大树下迎我。待我进屋安顿好,母亲忙着准备午饭,父亲说他还有些油菜桩子没挖完,趁天气还不算热赶快弄。母亲在老屋院墙旁边的水池里洗菜,可能发现遗忘了中午做汤时的配料,就叫喊一墙之隔正在挖油菜桩子的父亲:“哎,割点韭菜回来!”父亲听力越来越差,没应答。我赶忙说:“妈,让我去吧!”“拿那把豁口的旧菜刀啊!”母亲总不忘提醒,她似乎不记得女儿已过不惑。
我拿着豁口的菜刀直奔父母倾心侍弄的菜园:一行行,一垄垄,叶类蔬菜青翠欲滴,黄瓜、豇豆爬上插得齐整的瓜扦上,刚结的黄瓜才食指那么长,瓜尖上的黄花拢成一团,似乎舍不得与瓜孩子分离呢!辣椒结了不少,全似青青的灯笼;茄子正开着淡紫色的花,赏心悦目,这是开花蔬菜里少见的。
放眼菜园上方的旱地,只见玉米好像一排排小哨兵在站岗,腰杆挺得可直;玉米油黑发绿的叶子,随风摆动,发出簌簌的声音,像一曲撩人心弦的交响曲。青青的黄豆叶如一床厚厚的绿绒毯,你挨着我,我挤着你,竞赛般来迎接阳光雨露。
韭菜地明显分成两部:一部分已被割过,母亲用鸡屎灰均匀地铺撒在上面,韭菜头正倔强地冒出来,因被割的时间有先后,长得参差不齐,刚露出地表的呈现为黄绿色。另一部分则是碧玉妆成,修长的条叶摇曳生姿。我左手握住一把韭菜,右手用豁口的菜刀齐着根部横割过去,那韭菜真嫩,毫不费事!
此时,看着手中鲜嫩的韭菜,我有收获满满的感觉,不由得回忆起青少年时期从事农业劳动的情景。正是那些年的体力劳动,在我学习吴伯萧的《菜园小记》时,对田间地头的农业谚语和贴切动词有着更深的理解。
种菜第一步,撒菜秧子。平整一小块地,用手捏碎土疙瘩,再用淡粪水浇湿,然后向潮湿的土地上撒菜籽。为什么叫撒菜秧子呢?原来蔬菜种子除瓜豆类,颗粒多为娇小型,要等秧苗长到寸把高后移栽,所以要先育苗,撒菜秧子就代替撒菜籽成了口头语。
撒是重点,按照书面解释,就是把颗粒状的东西分散着扔出去。这可不容易,因为需要手的匀度和力度,弄不好撒不远,造成菜籽落到一处,发芽后拥挤得很;有的地儿却空空不见一棵。
菜籽撒匀后,或撒些薄土盖上;或用耙子扒一遍,便于菜籽与土地有机结合,如温度较高或较低,则会盖上稻草或麦秸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菜籽三五天即可发芽,钻出土壤,抛头露面,迎接阳光照耀,茁壮成长。
待菜秧子长到寸把高,即可移栽,不够粗壮的则被涮出来。“涮”的本意有两种:一是摇动着冲刷,略微洗洗;二是把肉片等放在滚水里烫一下取出蘸着佐料吃,遂有“涮火锅”一词。
此时的“涮”是引申出来的,即间隔着拔掉一些腰肢柔软的菜秧子,因秧苗脆嫩水灵,可炒着吃或汆汤用,也好度过菜荒。农谚“头伏萝卜二伏菜”说的应是西北地区,我的家乡则是“处暑萝卜白露菜”,因为萝卜和青菜都是喜欢凉爽气候的蔬菜,秋季播种过早,天热干旱,易生虫长不好;播种过迟,则因生长季节太短,不能充分长大。
母亲种萝卜是在地上间隔打凼(挖小坑),一个凼里撒上七八粒籽。等萝卜秧苗从小圆叶变成长叶再等三五天,就可涮萝卜菜了。细嫩的萝卜菜可腌着吃,早上吃稀饭真对口。一般而言,一个凼只留一棵萝卜菜,这样冬天拔萝卜时会足见其粗壮,故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说法。
为啥同样的叶类菜,采摘的动词又会不同呢?如挑(tiǎo)菠菜或撸菠菜、掐蕹菜(空心菜)、撇(piē)苦麻(谐音,具体菜名一直不清楚)、铲卷心菜、割(剪)韭菜呢?只有亲自去实践,才能掌握其用词的精准。记得小学有篇课文:“蔬菜的种类很多,有的吃根,有的吃茎,有的吃叶,有的吃果实。”
菠菜是根叶都可食用,红红的细根有丝丝的甜味,细细地咀嚼,更有味道。菠菜是秋末初冬播种,因山区气温低,成长速度慢,过年家家喜欢挑菠菜烫火锅吃。雪天或霜冻时挑菠菜可不容易,将剪刀尖头深插土里,用劲挑起(撸起),才不会弄断菜根。
空心菜因心空而得名,“掐”则一字传神,利用大拇指和食指的配合,轻轻用力即可折断。苦麻因苦涩而得名,是家乡用来喂鸡鸭猪的重要食材,此物生长迅速,一个生命周期能长高至一米出头。
“撇”的含义有多种,此处与“撇油沫儿”(从液面上轻轻地舀,以去掉泡沫或浮渣)类似,即用手从苦麻茎秆四周叶子顺序依次撕下,无需太大力度,否则容易弄断其重要的支撑物———茎秆。
卷心菜、包菜都是叶片层层裹起,形成团状硬球,一般选择用菜刀或铲子去弄断,以保证菜的完整性。韭菜无论是割剪,皆因其叶茎的形状,细密柔软。诗圣杜甫名篇《赠卫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时间匆匆,老友相聚,感慨万千,来顿简朴的饭局,既展示了诗人食人间烟火色,又展示了他友善好客情。
可能是因为豇豆、黄瓜属藤本植物,且果实细长,采摘时要用力拉扯,所以有扯豇豆、扯黄瓜之说。豆藤缠绕在豆扦上,茂盛时密不透风,钻进地里扯豇豆很受罪,出来衣服会湿透。黄瓜藤子更可怕,叶茎和叶片上都是毛茸茸的细刺,光着胳膊不小心碰到,会留下一道道红杠杠,火辣辣的疼。
记得儿时小伙伴们特别馋,黄瓜还只有拇指长,就趁大人们午休或晚上乘凉捉萤火虫之机,悄无声息地溜进菜园,摸到一根小黄瓜就扯,往往因用力过猛将瓜藤扯断一截。第二天,扯断的瓜藤经太阳照射,很快蔫死了,这必遭到大人们一顿臭骂,但小伙伴们谁也不会站出来告密。
辣椒、茄子等食果类蔬菜,属草本植物,无需攀高;葫芦、南瓜虽属藤本植物,但其体积大,有分量,往往摘取更合适。摘,取也,边观察边动手的劳动,当看到个别果实尚未成熟,就留下,只摘取成熟者。无论辣椒、茄子,还是葫芦、南瓜,采摘均待其长大可食用方去动手。
摘辣椒要特别注意,遇到雨水多的年份,有些辣椒从尖头腐烂,手碰到若不及时清洗,会染上“辣椒素”,像是有火在灼烧,即我们常说的“火辣辣”的感觉。获取黄豆角(gē)子选择用“拽”,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豆角与豆干难舍难分的场景,两手相互拉扯,决定胜负的当然是力道大的右手。
除了采摘蔬菜运用不同的动词,收种谷物的用词也不逊色。比如点豆子、掰六谷锤子(玉米棒子)、踩油菜、打麦子、倒芝麻、插红薯秧、剪红薯藤、捋红薯叶、挖红薯等等。
“点”一般是谷物颗粒较大,且播种是打凼(小坑),每凼一至四粒不等,有点数的意思。“掰”是象形字,左右各一只手,中间为分,即用两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六谷槌子长在高高的玉米秆上,个矮的人更需要双手举起,用力掰扯才能取到。“踩”是踩踏之意,成熟的油菜角(gē)子绽开需要用力,因其会戳手,人们往往选择用脚踩踏。
“打”是用物敲打,农村有一种器具(音为链该、链枷),用竹子削成长约30公分、宽约5公分的竹棍六七根,用绳子依次绑住连接,再利用卯榫的转动安装一长柄,供人有节奏地摇起,连续敲打麦穗,所以称打麦子。
“倒”字用在芝麻的收获上更为传神,从谚语“芝麻开花节节高”可知,芝麻结角(gē)是依次高攀。如何将成熟后割倒翻晒几日的芝麻籽从角(gē)子里顺利取出,似乎考验人们的脑力。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将扎捆的芝麻杆子轻而易举地倒过来,芝麻角(gē)子头朝下,用木棍轻轻敲打,黑色或白色的芝麻籽争先恐后地蹦出来,像是赶场子。
红薯很独特,粗嫩的叶杆可作蔬菜炒着吃,果头(块根)作为主食,既可生吃,也可蒸煮烧着吃。因其甜,老少皆爱。医学研究表明,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元物质,有抗癌、护心、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效,故誉为“长寿食品”。
红薯属草本植物,生命力顽强,栽培时可将藤子剪为几段,一头朝上,另一头用两指捏紧,轻轻插入土里。插红薯秧子最好选择雨后,一是土地潮湿容易插下去,二是新插的秧苗无需浇水滴根。
挖红薯的季节是秋末初冬,母亲会物尽其用,先剪红薯藤子,拉回家再捋(luō,用手握着条状红薯藤,顺着移动摘取)红薯叶子,最后将薯叶用柴火煮熟放入瓦缸,加少许盐腌渍贮藏,作为今冬明春喂猪的好饲料。挖红薯的“挖”可是技术活,红薯埋在土里,要观察红薯周围土层裂度和隆起度,挖掘范围要准,锄头下去要深,否则红薯会被腰斩,挖坏的红薯则不易储存。
得益于回家探亲,我有机会在蔬菜瓜果旺盛季节走进菜园,曾经的记忆一下清晰起来,每一种蔬菜,每一样谷物,采摘时可使用不同的动词。但随着城市化和机械化的进程,农事中这些丰富具体的形象动词,终将渐行渐远,淡出大部分人的视野,只是书本上一个抽象的词汇而已。对那些从未稼穑的孩子们而言,他们将更难理解汉字的神奇与魅力了。
?精华推荐?
咸菜中的宠儿——雪里蕻
乡村六月好时节菜籽油香飘万家
赞赏
| |